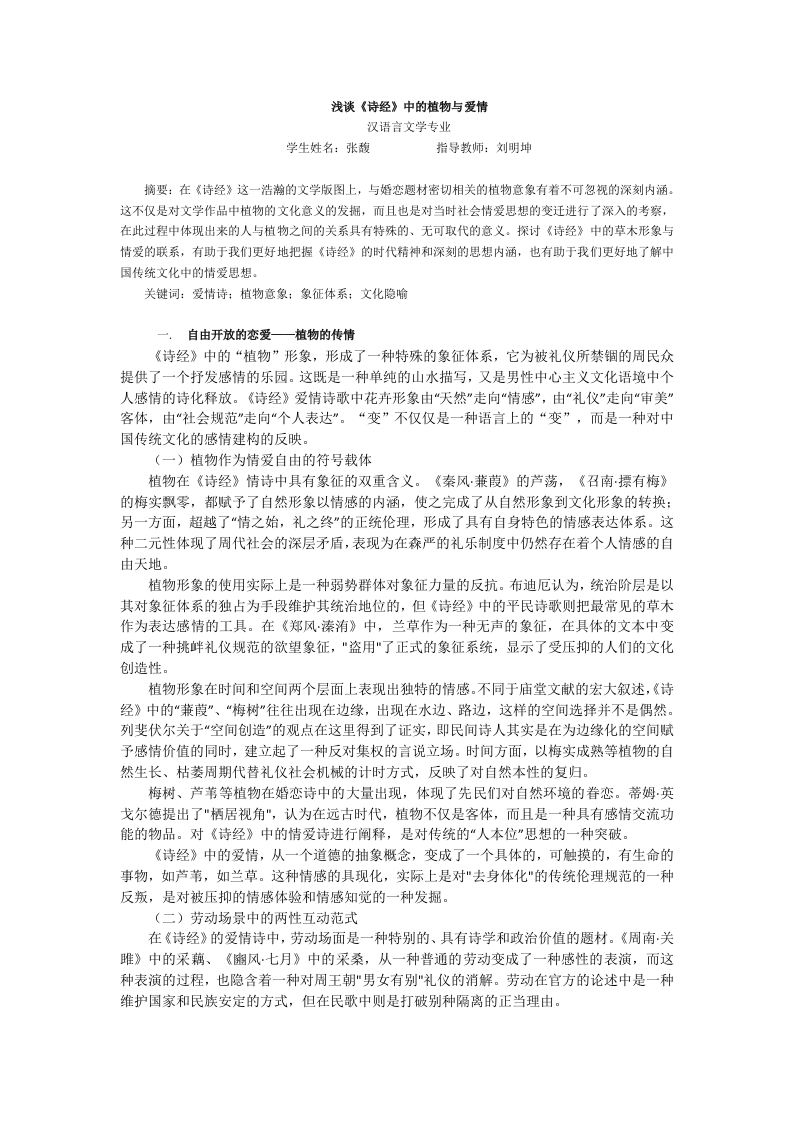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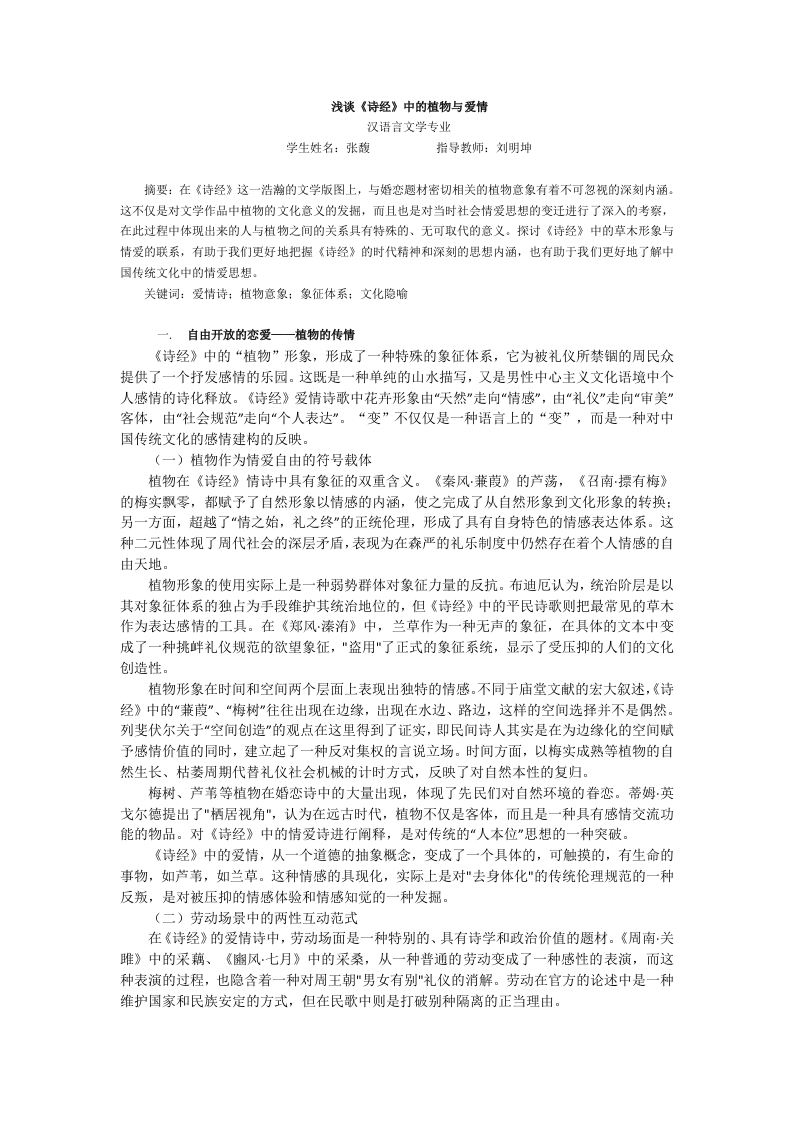
第1页 / 共8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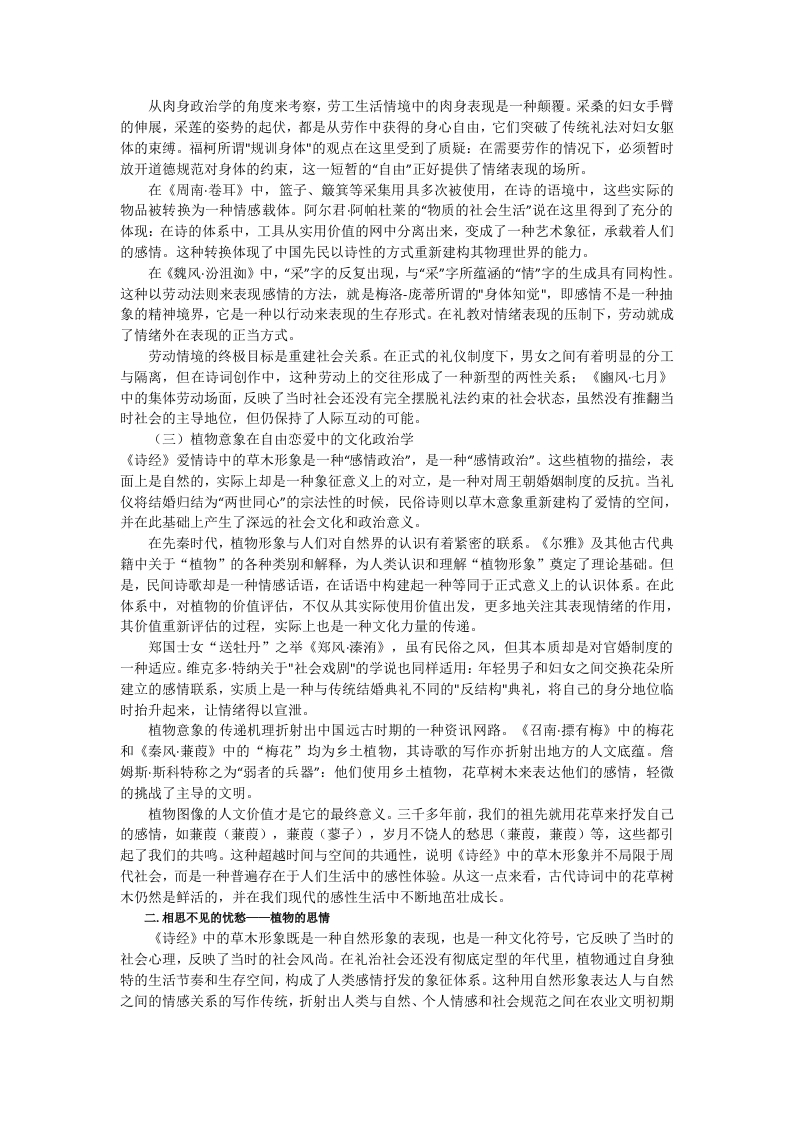
第2页 / 共8页

第3页 / 共8页

第4页 / 共8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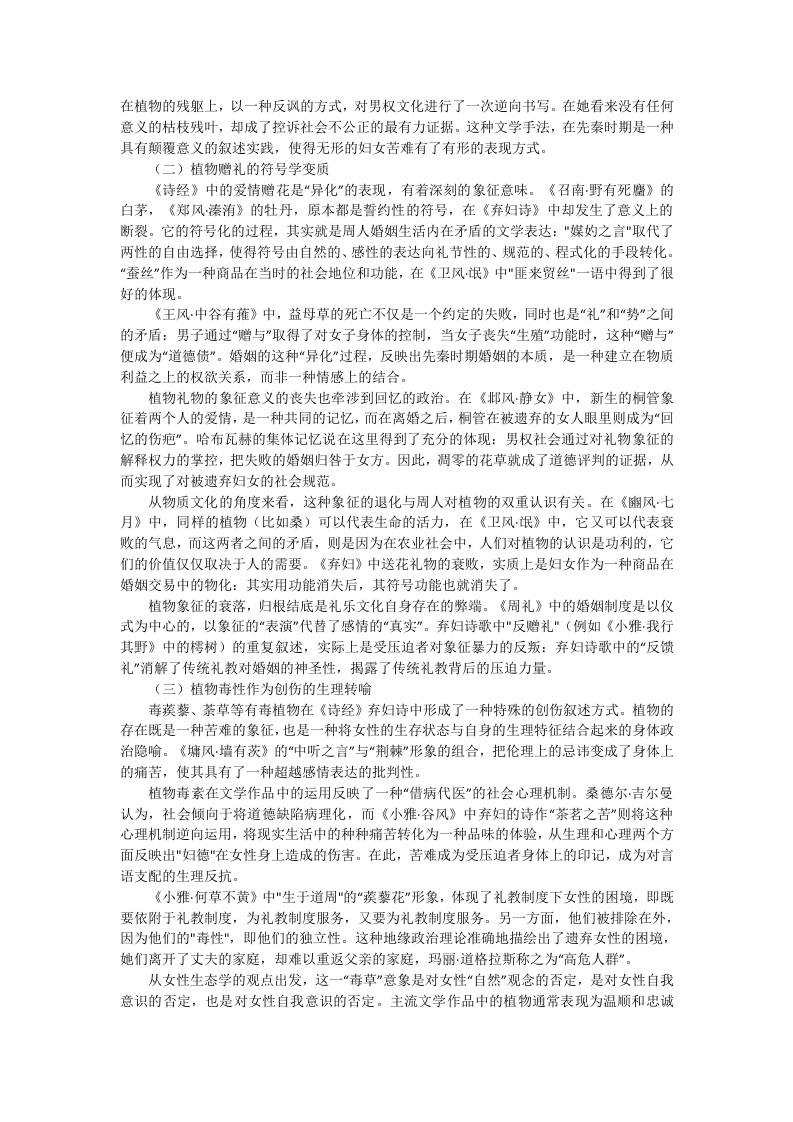
第5页 / 共8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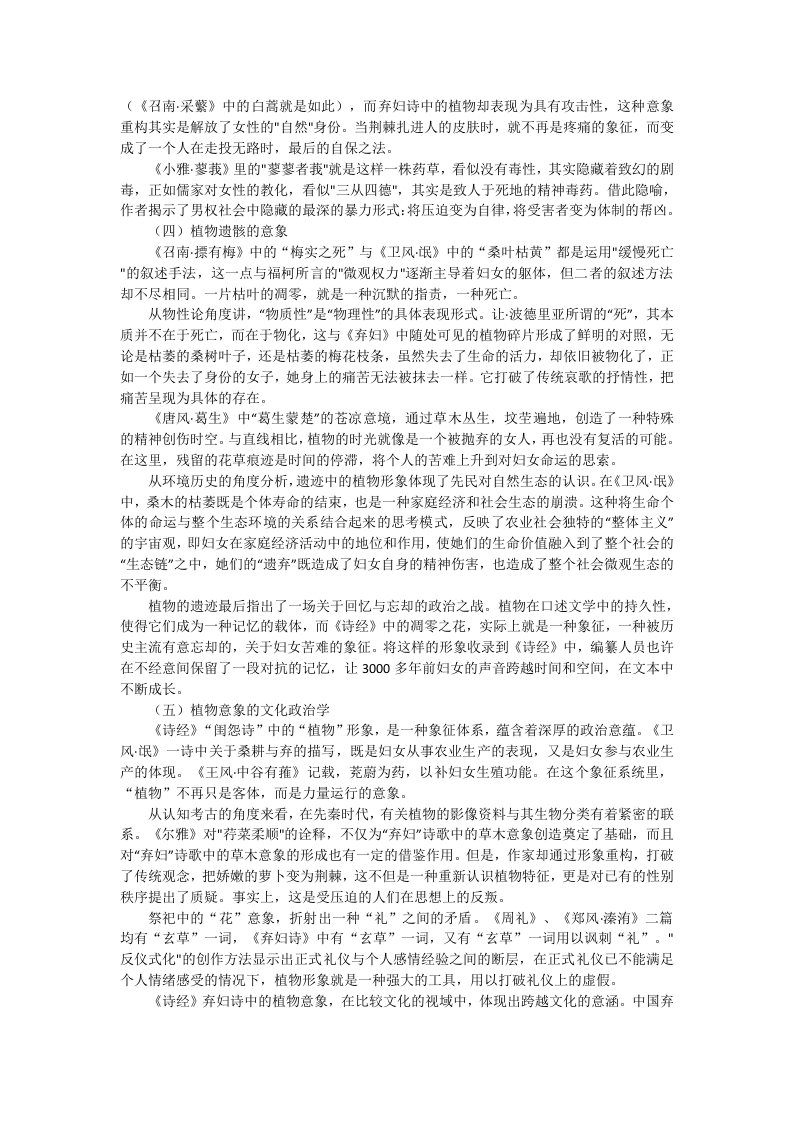
第6页 / 共8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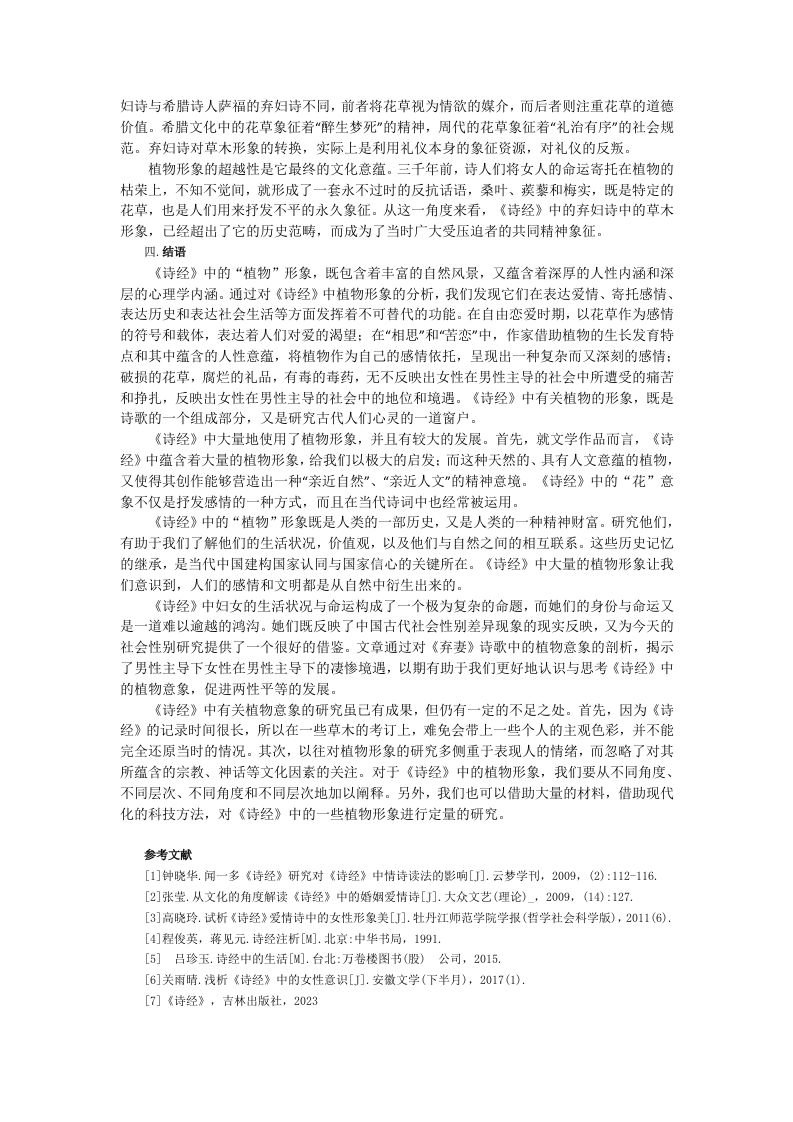
第7页 / 共8页
试读已结束,还剩1页,您可下载完整版后进行离线阅读
浅谈《诗经》中的植物与爱情此内容为付费资源,请付费后查看
黄金会员免费钻石会员免费
付费资源
© 版权声明
文章版权归作者所有,未经允许请勿转载。
THE END
浅谈《诗经》中的植物与爱情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姓名:张馥指导教师:刘明坤摘要:在《诗经》这一浩瀚的文学版图上,与婚恋趣材密切相关的植物意象有着不可忽视的深刻内涵。这不仅是对文学作品中植物的文化意义的发掘,而且也是对当时社会情爱思想的变迁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在此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人与植物之间的关系具有特殊的、无可取代的意义。探讨《诗经》中的草木形象与情爱的联系,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诗经》的时代精神和深刻的思想内涵,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情爱思想。关键词:爱情诗:植物意象:象征体系:文化隐喻一.自由开放的恋爱——植物的传情《诗经》中的“植物”形象,形成了一种特殊的象征体系,它为被礼仪所禁锢的周民众提供了一个抒发感情的乐园。这既是一种单纯的山水描写,又是男性中心主义文化语境中个人感情的诗化释放。《诗经》爱情诗歌中花卉形象由“天然“走向“情感”,由“礼仪“走向“审美”客体,由“社会规范走向“个人表达”。“变”不仅仅是一种语言上的“变”,而是一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感情建构的反映。(一)植物作为情爱自由的符号载体植物在《诗经》情诗中具有象征的双重含义。《秦风·兼葭》的芦荡,《召南摽有梅》的梅实飘零,都赋予了自然形象以情感的内函,使之完成了从自然形象到文化形象的转换:另一方面,超越了“情之始,礼之终”的正统伦理,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情感表达体系。这种二元性体现了周代社会的深层矛盾,表现为在森严的礼乐制度中仍然存在着个人情感的自由天地。植物形象的使用实际上是一种弱势群体对象征力量的反抗。布迪厄认为,统治阶层是以其对象征体系的独占为手段维护其统治地位的,但《诗经》中的平民诗歌则把最常见的草木作为表达感情的工具。在《郑风溱洧》中,兰草作为一种无声的象征,在具体的文本中变成了一种挑衅礼仪规范的欲望象征,“盗用“了正式的象征系统,显示了受压抑的人们的文化创造性。植物形象在时间和空间两个层面上表现出独特的情感。不同于庙堂文献的宏大叙述,《诗经》中的“兼葭”、“梅树”往往出现在边缘,出现在水边、路边,这样的空间选择并不是偶然。列斐伏尔关于“空间创造”的观点在这里得到了证实,即民间诗人其实是在为边缘化的空间赋予感情价值的同时,建立起了一种反对集权的言说立场。时间方面,以梅实成熟等植物的自然生长、枯萎周期代替礼仪社会机械的计时方式,反映了对自然本性的复归。梅树、芦苇等植物在婚恋诗中的大量出现,体现了先民们对自然环境的眷恋。蒂姆·英戈尔德提出了“栖居视角“,认为在远古时代,植物不仅是客体,而且是一种具有感情交流功能的物品。对《诗经》中的情爱诗进行阐释,是对传统的“人本位”思想的一种突破。《诗经》中的爱情,从一个道德的抽象概念,变成了一个具体的,可触摸的,有生命的事物,如芦苇,如兰草。这种情感的具现化,实际上是对"去身体化"的传统伦理规范的一种反叛,是对被压抑的情感体验和情感知觉的一种发掘。(二)劳动场景中的两性互动范式在《诗经》的爱情诗中,劳动场面是一种特别的、具有诗学和政治价值的题材。《周南·关雎》中的采藕、《豳风七月》中的采桑,从一种普通的劳动变成了一种感性的表演,而这种表演的过程,也隐含着一种对周王朝“男女有别“礼仪的消解。劳动在官方的论述中是一种维护国家和民族安定的方式,但在民歌中则是打破别种隔离的正当理由。从肉身政治学的角度来考察,劳工生活情境中的肉身表现是一种颠覆。采桑的妇女手臂的伸展,采莲的姿势的起伏,都是从劳作中获得的身心自由,它们突破了传统礼法对妇女躯体的束缚。福柯所谓"规训身体“的观点在这里受到了质疑:在需要劳作的情况下,必须暂时放开道德规范对身体的约束,这一短暂的“自由”正好提供了情绪表现的场所。在《周南卷耳》中,篮子、簸箕等采集用具多次被使用,在诗的语境中,这些实际的物品被转换为一种情感载体。阿尔君阿帕杜莱的“物质的社会生活”说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诗的体系中,工具从实用价值的网中分离出来,变成了一种艺术象征,承载着人们的感情。这种转换体现了中国先民以诗性的方式重新建构其物理世界的能力。在《魏风汾沮洳》中,“采”字的反复出现,与“采”字所蕴涵的“情”字的生成具有同构性。这种以劳动法则来表现感情的方法,就是梅洛-庞蒂所谓的"身体知觉“,即感情不是一种抽象的精神境界,它是一种以行动来表现的生存形式。在礼教对情绪表现的压制下,劳动就成了情绪外在表现的正当方式。劳动情境的终极目标是重建社会关系。在正式的礼仪制度下,男女之间有着明显的分工与隔离,但在诗词创作中,这种劳动上的交往形成了一种新型的两性关系:《豳风七月》中的集体劳动场面,反映了当时社会还没有完全摆脱礼法约束的社会状态,虽然没有推翻当时社会的主导地位,但仍保持了人际互动的可能。(三)植物意象在自由恋爱中的文化政治学《诗经》爱情诗中的草木形象是一种“感情政治”,是一种“感情政治”。这些植物的描绘,表面上是自然的,实际上却是一种象征意义上的对立,是一种对周王朝婚姻制度的反抗。当礼仪将结婚归结为“两世同心”的宗法性的时候,民俗诗则以草木意象重新建构了爱情的空间,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深远的社会文化和政治意义。在先秦时代,植物形象与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有着紧密的联系。《尔雅》及其他古代典籍中关于“植物”的各种类别和解释,为人类认识和理解“植物形象”奠定了理论基础。但是,民间诗歌却是一种情感话语,在话语中构建起一种等同于正式意义上的认识体系。在此体系中,对植物的价值评估,不仅从其实际使用价值出发,更多地关注其表现情绪的作用,其价值重新评估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种文化力量的传递。郑国士女“送牡丹”之举《郑风溱洧》,虽有民俗之风,但其本质却是对宫婚制度的种适应。维克多特纳关于“社会戏剧"的学说也同样适用:年轻男子和妇女之间交换花朵所建立的感情联系,实质上是一种与传统结婚典礼不同的"反结构"典礼,将自己的身分地位临时抬升起来,让情绪得以宣泄。植物意象的传递机理折射出中国远古时期的一种资讯网路。《召南標有梅》中的梅花和《秦风·蒹葭》中的“梅花”均为乡土植物,其诗歌的写作亦折射出地方的人文底蕴。詹姆斯斯科特称之为“弱者的兵器”:他们使用乡土植物,花草树木来表达他们的感情,轻微的挑战了主导的文明。植物图像的人文价值才是它的最终意义。三千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就用花草来抒发自己的感情,如兼葭(兼葭),兼葭(蓼子),岁月不饶人的愁思(兼葭,兼葭)等,这些都引起了我们的共鸣。这种超越时间与空间的共通性,说明《诗经》中的草木形象并不局限于周代社会,而是一种普遍存在于人们生活中的感性体验。从这一点来看,古代诗词中的花草树木仍然是鲜活的,并在我们现代的感性生活中不新地茁壮成长。二.相思不见的忧愁—植物的思情《诗经》中的草木形象既是一种自然形象的表现,也是一种文化符号,它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心理,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尚。在礼治社会还没有彻底定型的年代里,植物通过自身独特的生活节奏和生存空间,构成了人类感情抒发的象征体系。这种用自然形象表达人与自然之间的情感关系的写作传统,折射出人类与自然、个人情感和社会规范之间在农业文明初期的一场复杂的游戏。(一)植物作为情爱自由的符号载体《诗经》中的“植物象征”,实质上是周人民对自然界进行的一种精神上的变革,是对人类自身的一种“转化”。当人们在芦苇、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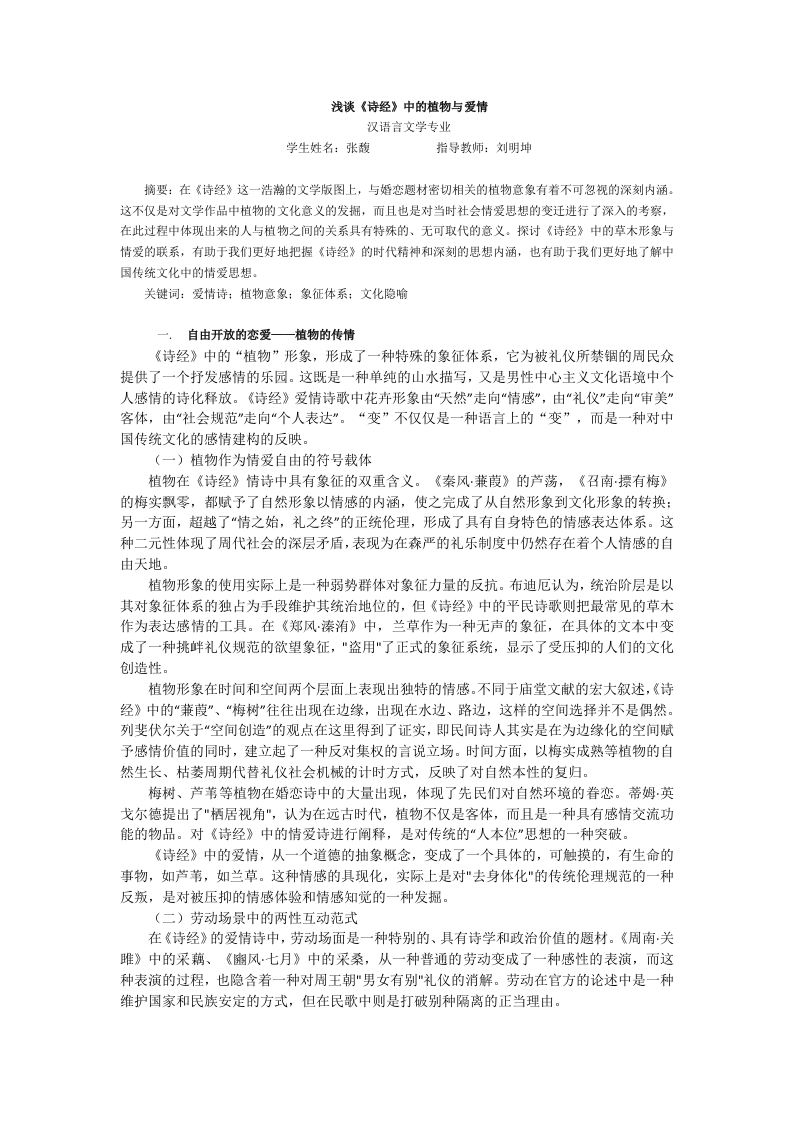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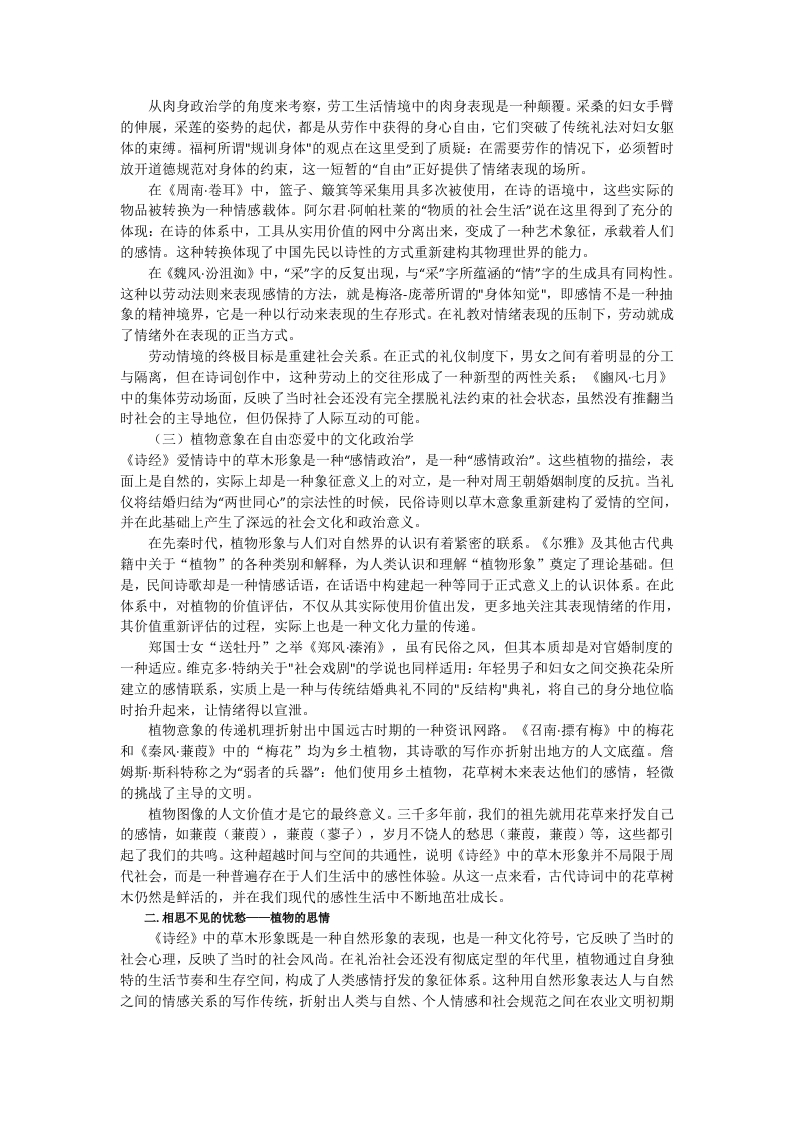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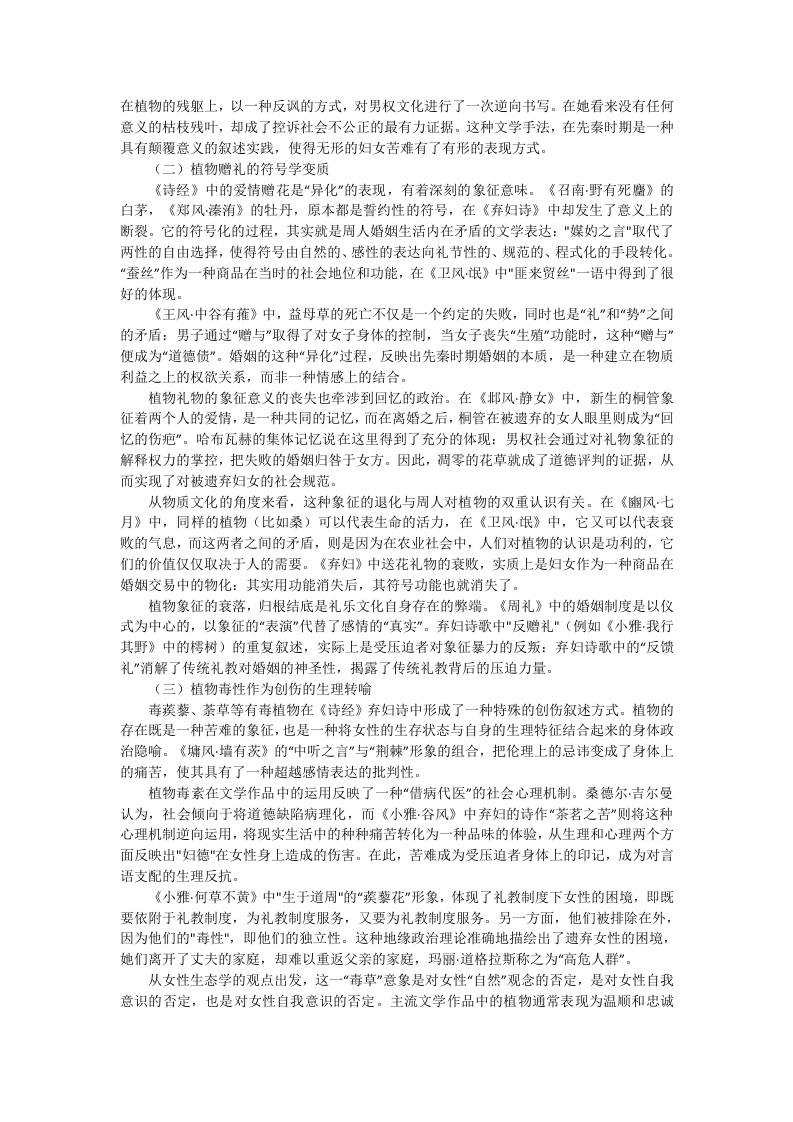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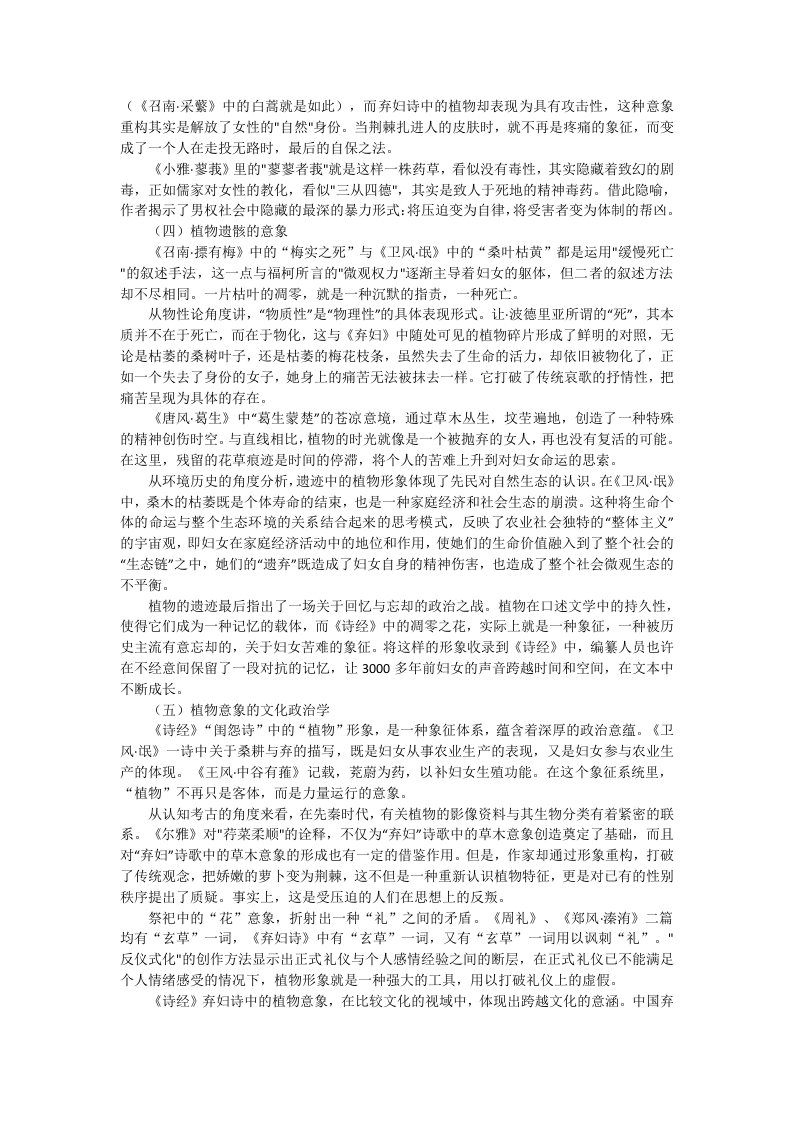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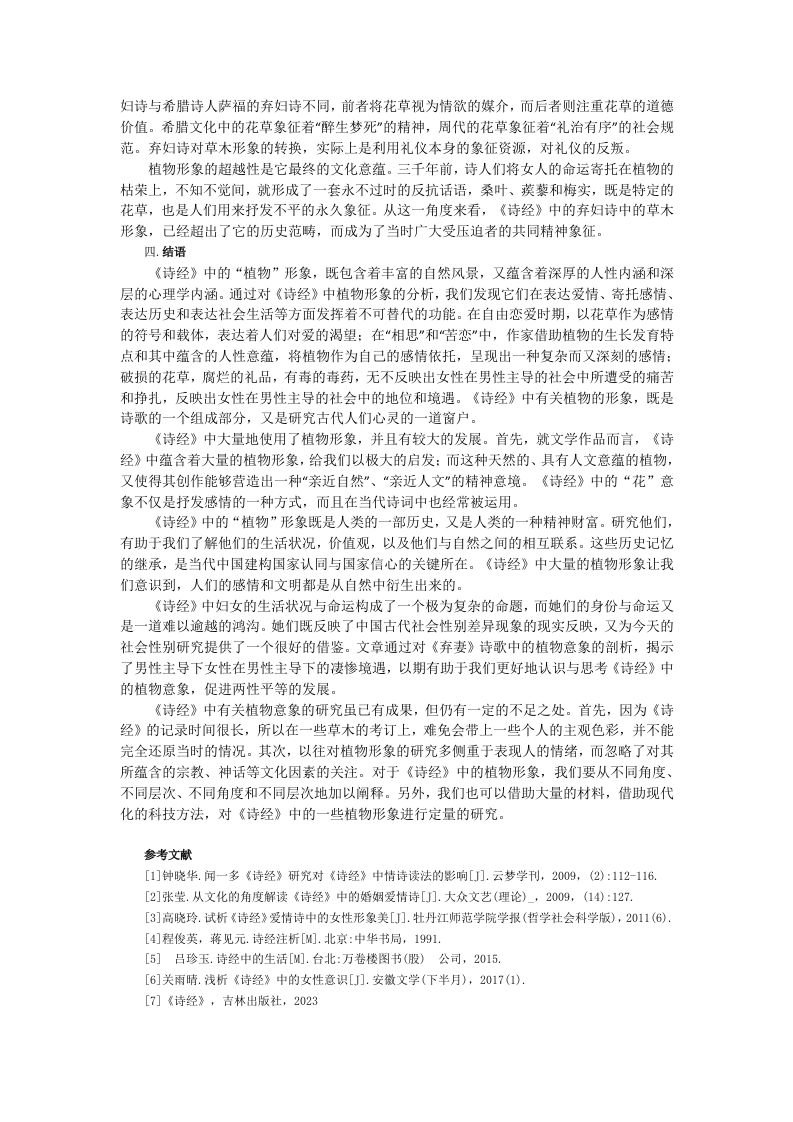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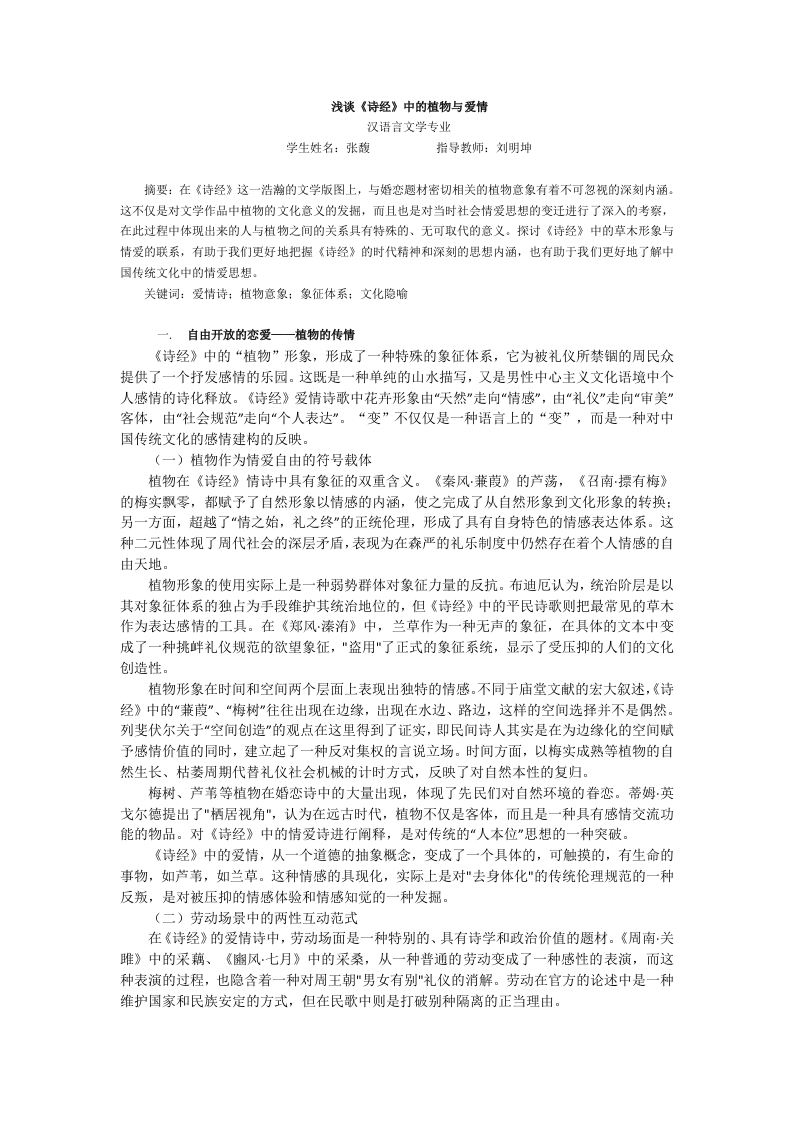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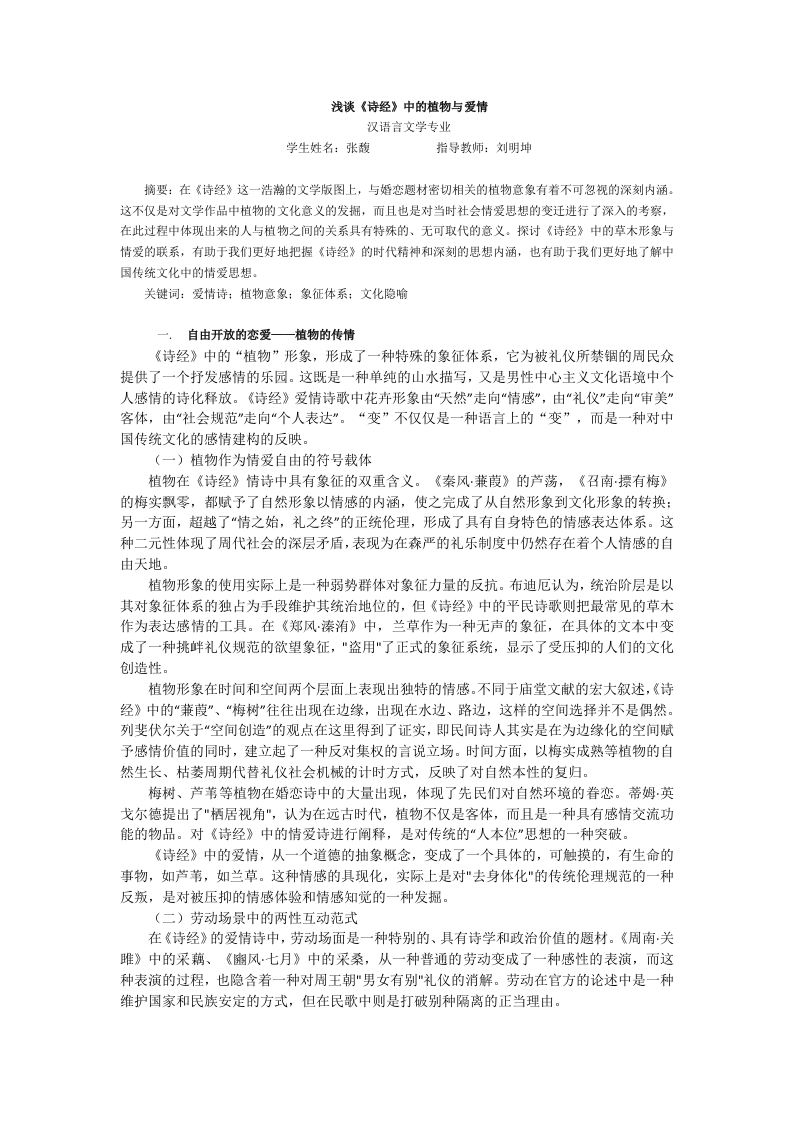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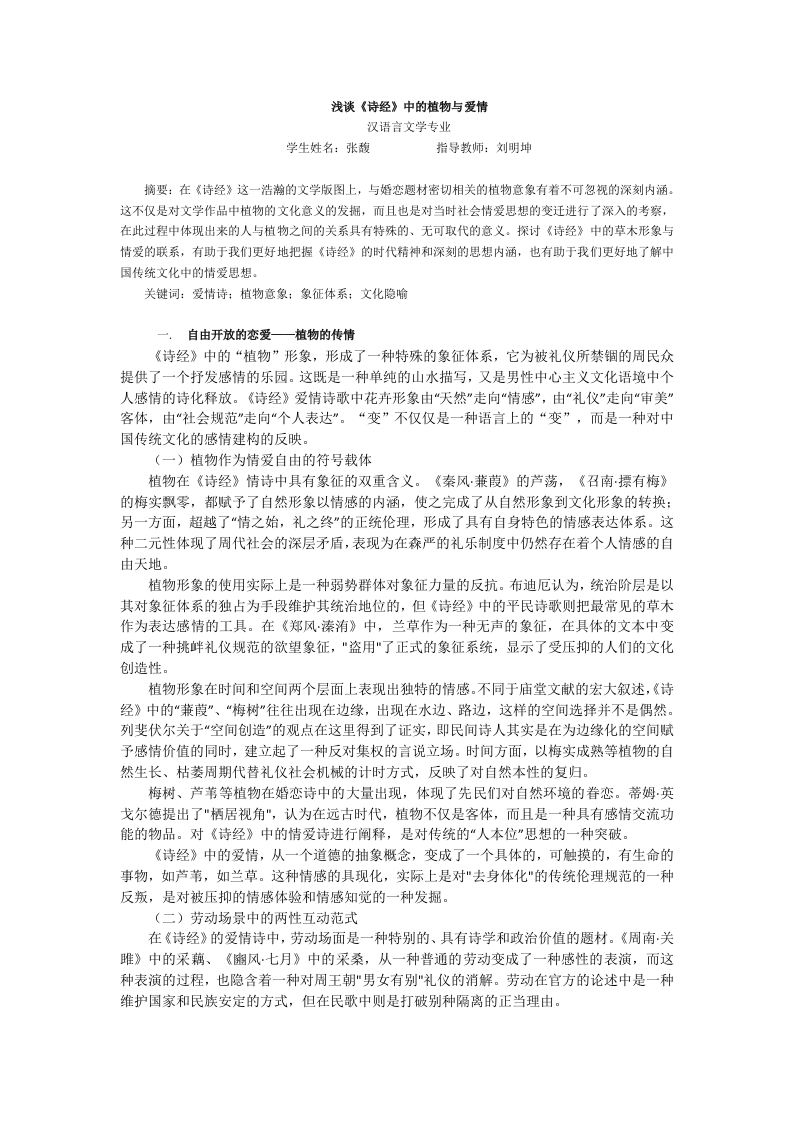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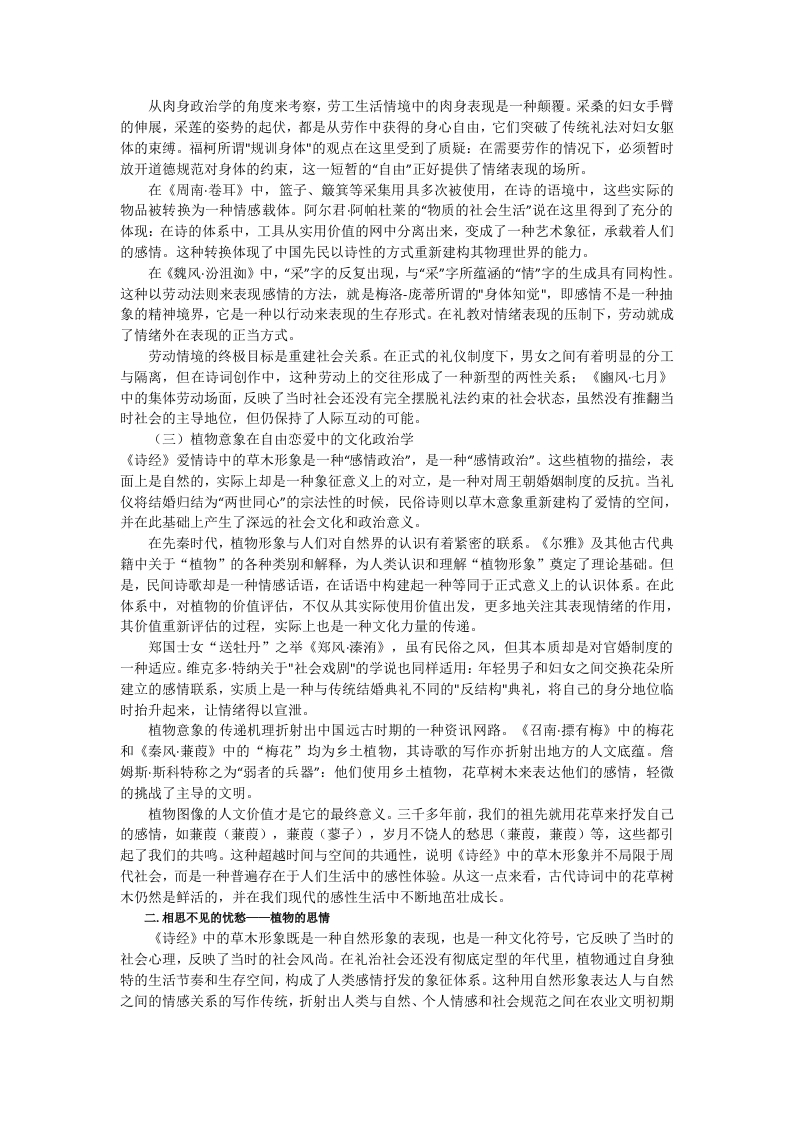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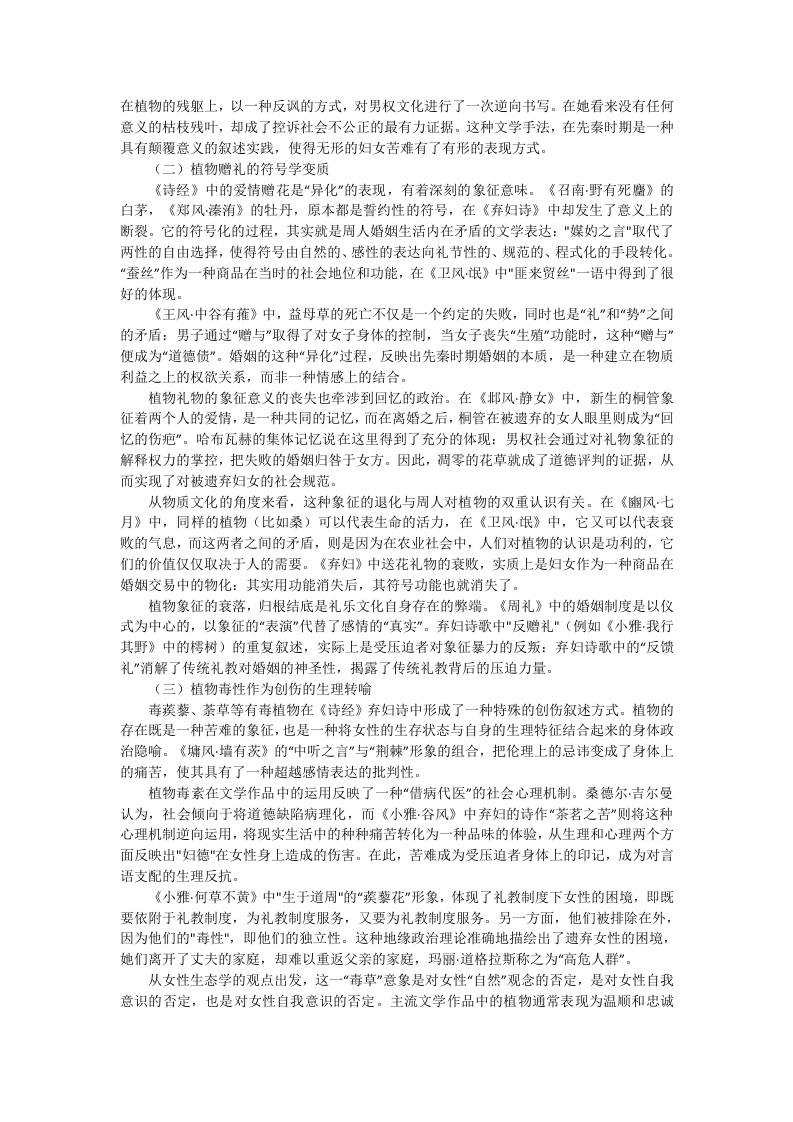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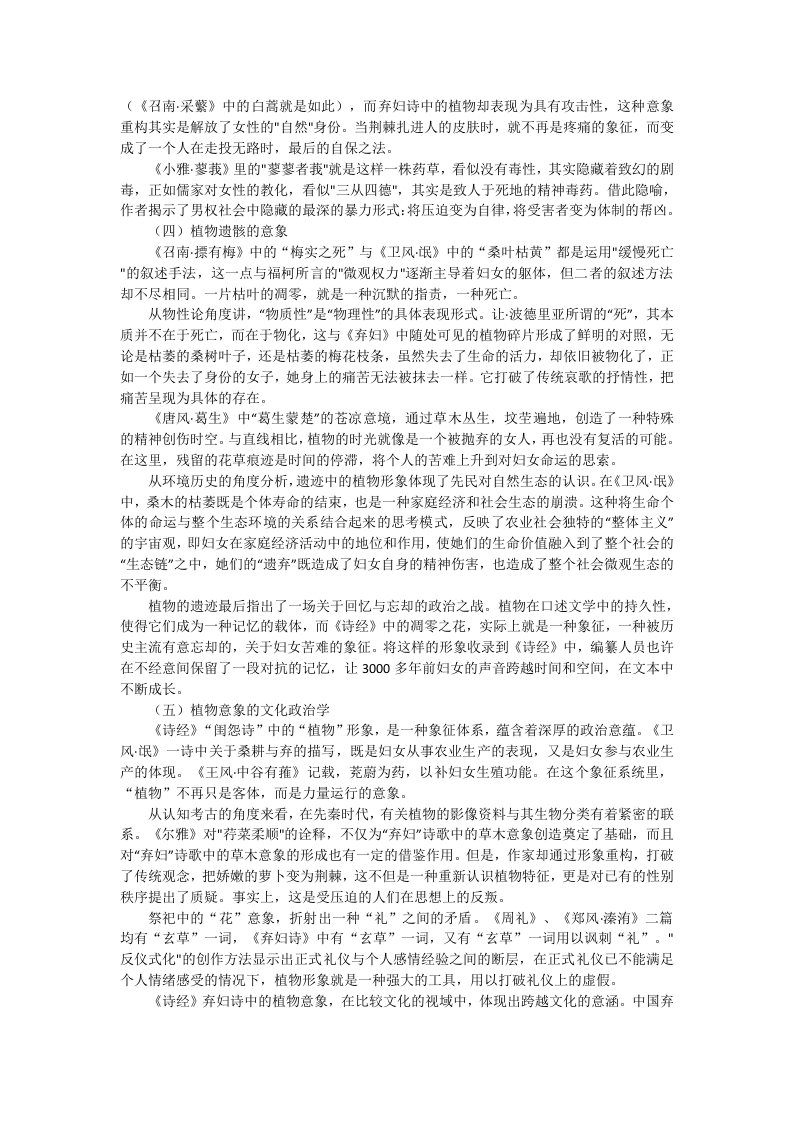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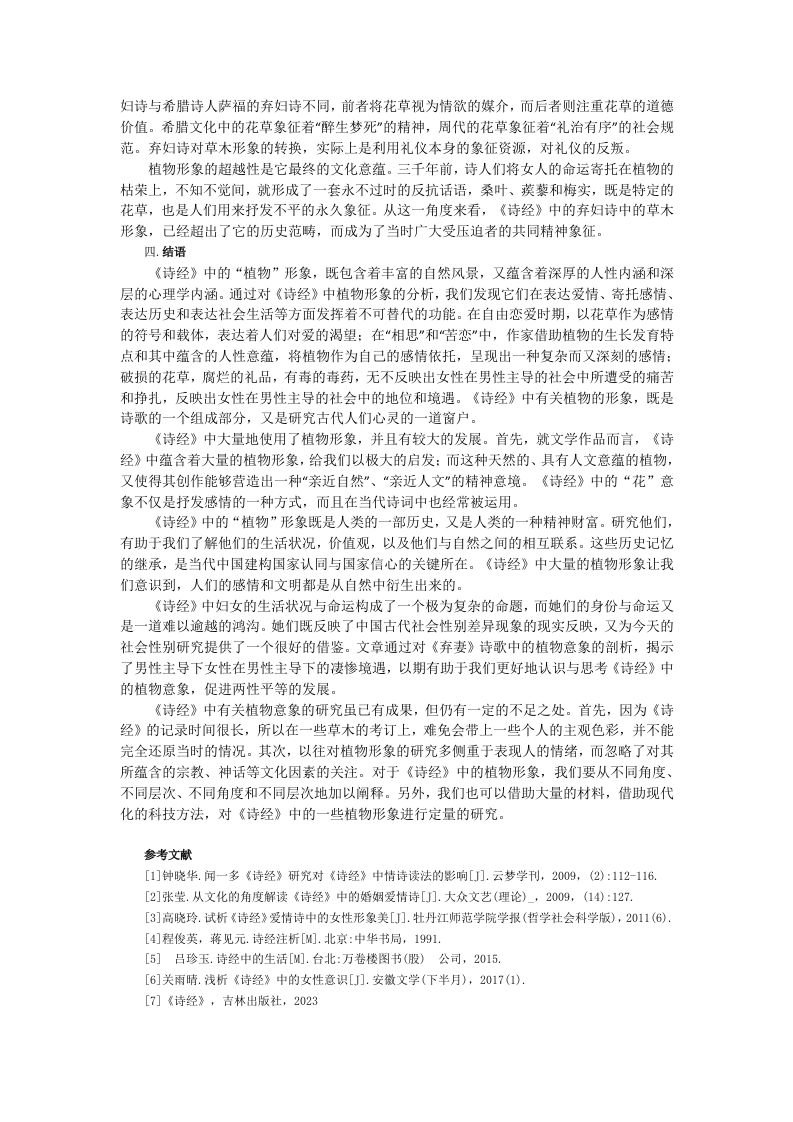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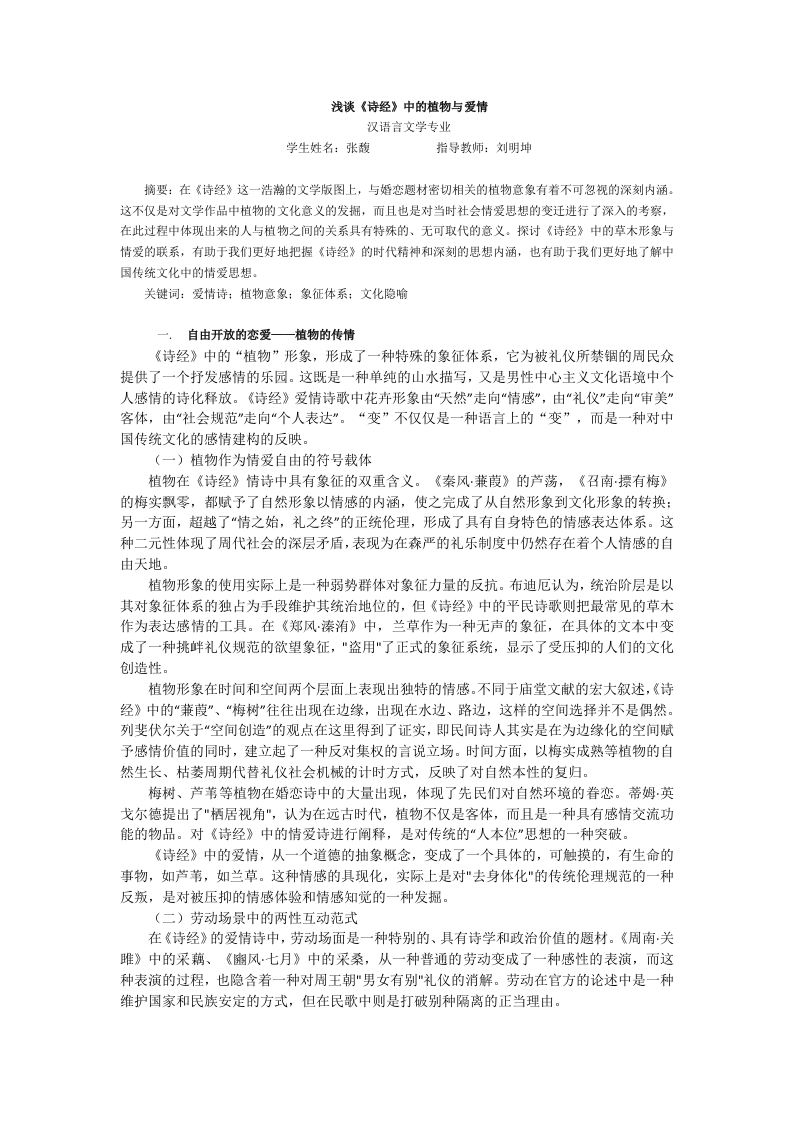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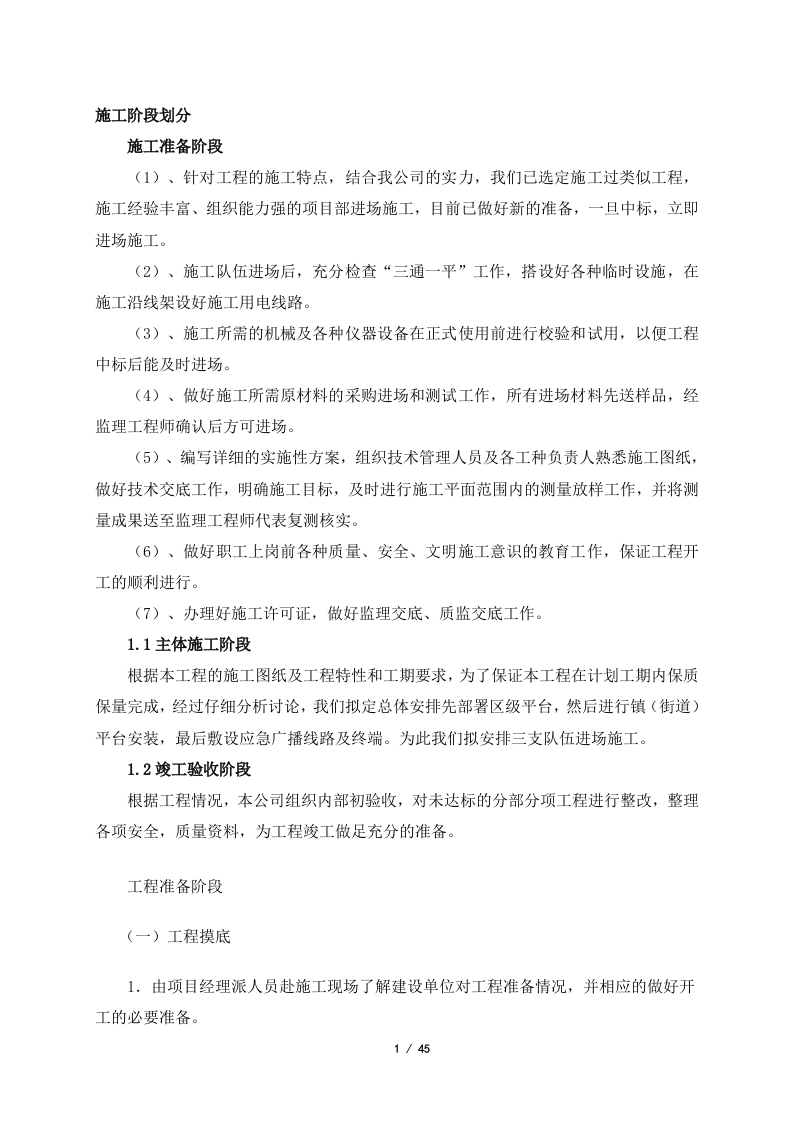
暂无评论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