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页 / 共1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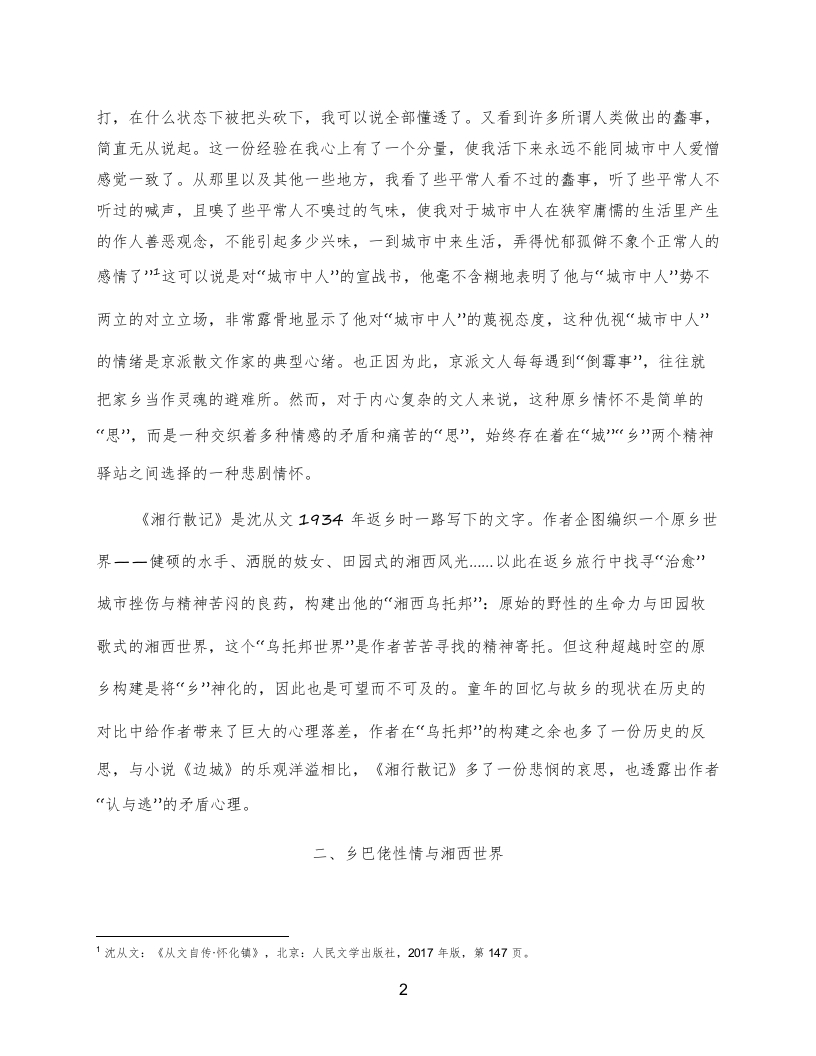
第2页 / 共1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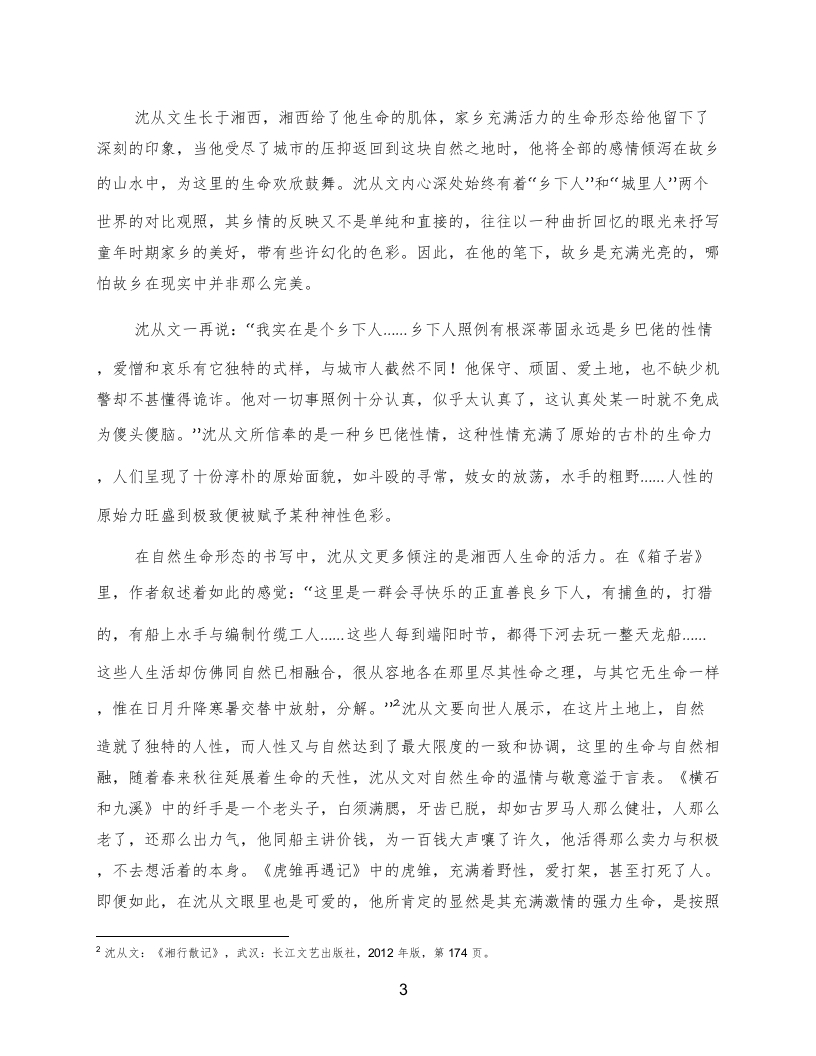
第3页 / 共1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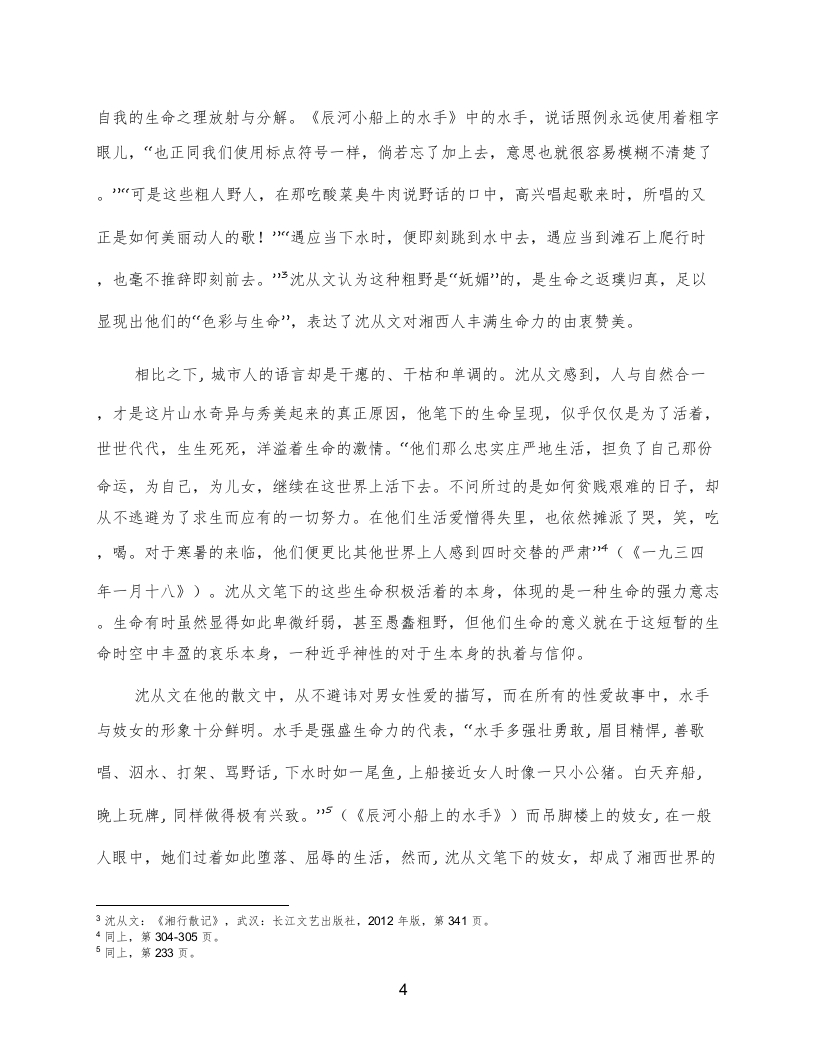
第4页 / 共1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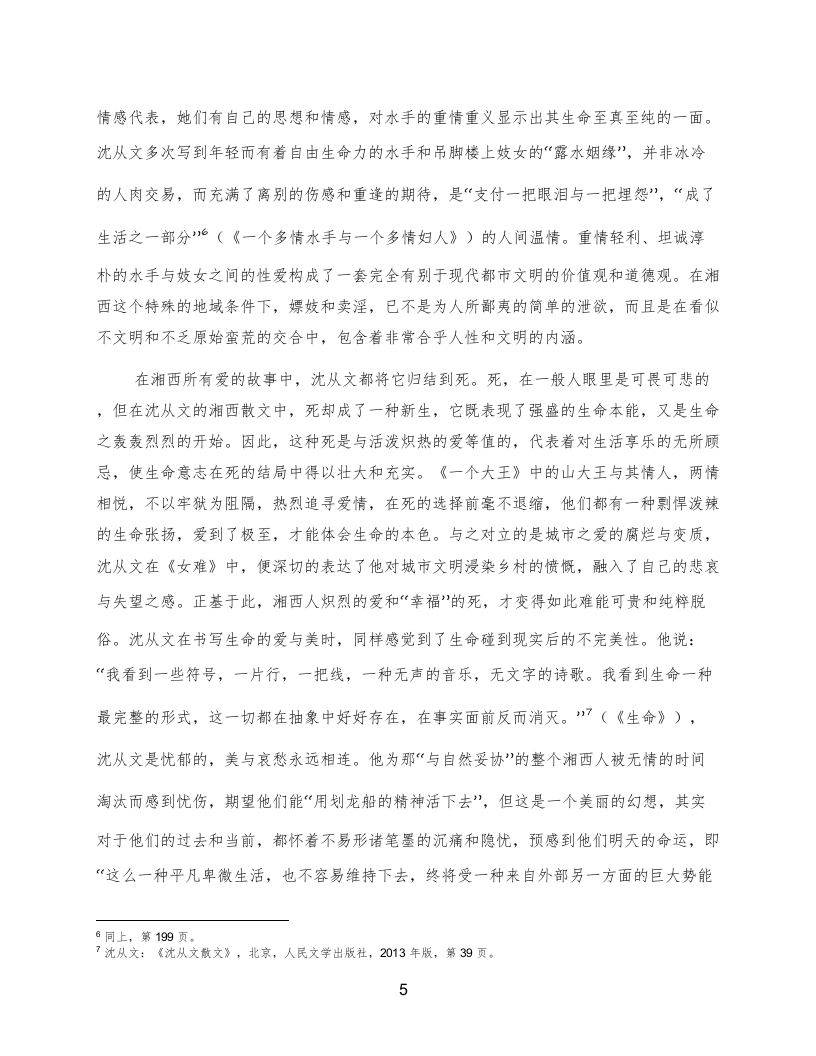
第5页 / 共1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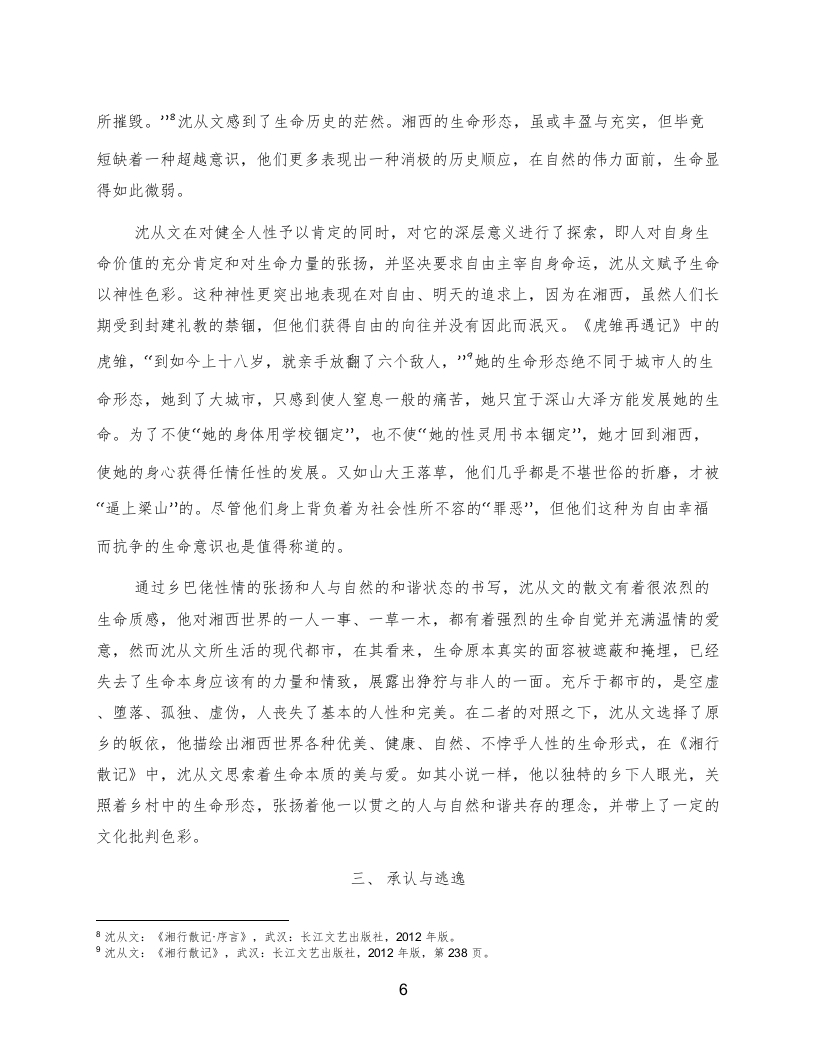
第6页 / 共1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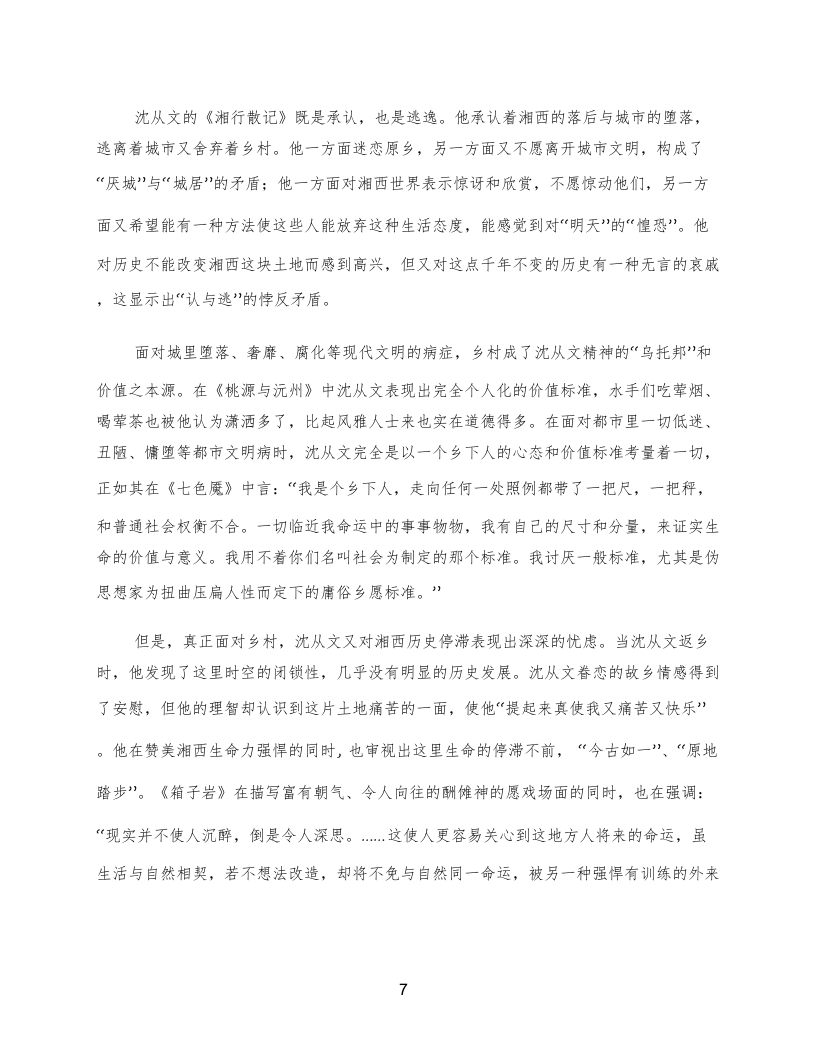
第7页 / 共10页
试读已结束,还剩3页,您可下载完整版后进行离线阅读
原乡的皈依与时空的逃逸——试论沈从文《湘行散记》“湘西乌托邦”构建的两层意蕴_沈从文《湘行散记》此内容为付费资源,请付费后查看
黄金会员免费钻石会员免费
付费资源
© 版权声明
文章版权归作者所有,未经允许请勿转载。
THE END
原乡的皈依与时空的逃逸一一试论沈从文《湘行散记》“湘西鸟托邦”构建的两层意蕴内容提要《湘行散记》是沈从文1934年返乡时一路写下的文字。作者企图编织一个原乡世界一一健硕的水手、洒脱的妓女、田园式的湘西风光.以此在返乡旅行中找寻“治愈”城市挫伤与精神苦闷的良药,构建出他的“湘西鸟托邦”:原始的野性的生命力与田园牧歌式的湘西世界,这个“鸟托邦世界”是作者苦苦寻找的精神寄托。但这种超越时空的原乡构建是将“乡”神化的,因此也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童年的回忆与故乡的现状在历史的对比中给作者带来了巨大的心理落差,作者在“鸟托邦”的构建之余也多了一份历史的反思,与小说《边城》的乐观洋溢相比,《湘行散记》多了一份悲悯的哀思,也透露出作者“认与逃”的矛盾心理。关镀词原乡;皈依;时空;逃逸;沈从文《湘行散记》:湘西鸟托邦一、引言从上世纪二十年代未开始,在北京逐渐形成了一个松散但却很有特色的作家群,时人称之为“京派作家”,京派文人一个大致相同的人生经历是:从乡村来到城里,且常常以乡下人自居,有着强烈的乡下人情结,他们背井离乡,出家远游,带着对都市的幻想出走乡村,来到城市。对于一个漂泊外乡的游子来说,其情感的反映方式难免有对家乡的思念,再加之当时的都市充斥着冷漠且市侩气十足,给来自乡间的京派文人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压抑,并一度产生了情感的危机和悬空状态。严酷的现实碾压了他们的尊严和梦,强化了他们内心深处对家乡的怀念,也刺激了“自我”与城市的对立。沈从文作为京派文人的领衔者,表现出鲜明的皈依原乡的立场,他在散文中这样放肆地写道:“我在那地约一年零四个月,大致眼看杀过七百人。一些人在什么情形下被拷1打,在什么状态下被把头砍下,我可以说全部懂透了。又看到许多所谓人类做出的蠢事,筒直无从说起。这一份经验在我心上有了一个分量,使我活下来永远不能同城市中人爱憎感觉一致了。从那里以及其他一些地方,我看了些平常人看不过的蠢事,听了些平常人不听过的喊声,且嗅了些平常人不嗅过的气味,使我对于城市中人在狭窄庸懦的生活里产生的作人善恶观念,不能引起多少兴味,一到城市中来生活,弄得忧郁孤僻不象个正常人的感情了江这可以说是对“城市中人”的宣战书,他毫不含糊地表明了他与“城市中人”势不两立的对立立场,非常露骨地显示了他对“城市中人”的蔑视态度,这种仇视“城市中人”的情绪是京派散文作家的典型心绪。也正因为此,京派文人每每遇到“倒霉事”,往往就把家乡当作灵魂的避难所。然而,对于内心复杂的文人来说,这种原乡情怀不是筒单的“思”,而是一种交织着多种情感的矛盾和痛苦的“思”,始终存在着在“城“乡”两个精神驿站之间选择的一种悲剧情怀。《湘行散记》是沈从文1934年返乡时一路写下的文字。作者企图编织一个原乡世界一一健硕的水手、洒脱的妓女、田园式的湘西风光.以此在返乡旅行中找寻“治愈”城市挫伤与精神苦闷的良药,构建出他的“湘西鸟托邦”:原始的野性的生命力与田园牧歌式的湘西世界,这个“鸟托邦世界”是作者苦苦寻找的精神寄托。但这种超越时空的原乡构建是将“乡”神化的,因此也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童年的回忆与故乡的现状在历史的对比中给作者带来了巨大的心理落差,作者在“鸟托邦”的构建之余也多了一份历史的反思,与小说《边城》的乐观洋溢相比,《湘行散记》多了一份悲悯的哀思,也透露出作者“认与逃”的矛盾心理。二、乡巴佬性情与湘西世界1沈从文:《从文自传怀化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47页。2沈从文生长于湘西,湘西给了他生命的肌体,家乡充满活力的生命形态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他受尽了城市的压抑返回到这块自然之地时,他将全部的感情倾泻在故乡的山水中,为这里的生命欢欣鼓舞。沈从文内心深处始终有着“乡下人”和“城里人”两个世界的对比观照,其乡情的反映又不是单纯和直接的,往往以一种曲折回忆的眼光来抒写童年时期家乡的美好,带有些许幻化的色彩。因此,在他的笔下,故乡是充满光亮的,哪怕故乡在现实中并非那么完美。沈从文一再说:“我实在是个乡下人…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爱憎和哀乐有它独特的式样,与城市人截然不同!他保守、顽固、爱土地,也不缺少机警却不甚懂得诡诈。他对一切事照例十分认真,似乎太认真了,这认真处某一时就不免成为傻头傻脑。”沈从文所信奉的是一种乡巴佬性情,这种性情充满了原始的古朴的生命力,人们呈现了十份淳朴的原始面貌,如斗殴的寻常,妓女的放荡,水手的粗野…人性的原始力旺盛到极致便被赋予某种神性色彩。在自然生命形态的书写中,沈从文更多倾注的是湘西人生命的活力。在《箱子岩》里,作者叙述着如此的感觉:“这里是一群会寻快乐的正直善良乡下人,有捕鱼的,打猎的,有船上水手与编制竹缆工人这些人每到端阳时节,都得下河去玩一整天龙船…这些人生活却仿佛同自然已相融合,很从容地各在那里尽其性命之理,与其它无生命一样,惟在日月升降寒暑交替中放射,分解。2沈从文要向世人展示,在这片土地上,自然造就了独特的人性,而人性又与自然达到了最大限度的一致和协调,这里的生命与自然相融,随着春来秋往延展着生命的天性,沈从文对自然生命的温情与敏意溢于言表。《横石和九溪》中的纤手是一个老头子,白须满腮,牙齿已脱,却如古罗马人那么健壮,人那么老了,还那么出力气,他同船主讲价钱,为一百钱大声嚷了许久,他活得那么卖力与积极,不去想活着的本身。《虎雏再遇记》中的虎雏,充满着野性,爱打架,甚至打死了人。即便如此,在沈从文眼里也是可爱的,他所肯定的显然是其充满激情的强力生命,是按照2沈从文:《湘行做记》,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174页。3自我的生命之理放射与分解。《辰河小船上的水手》中的水手,说话照例永远使用着粗字眼儿,“也正同我们使用标点符号一样,倘若忘了加上去,意思也就很容易模糊不清楚了。“可是这些粗人野人,在那吃酸菜臭牛肉说野话的口中,高兴唱起歌来时,所唱的又正是如何美丽动人的歌!“遇应当下水时,便即刻跳到水中去,遇应当到滩石上爬行时,也毫不推辞即刻前去。3沈从文认为这种粗野是“妩媚”的,是生命之返璞归真,足以显现出他们的“色彩与生命”,表达了沈从文对湘西人丰满生命力的由衷赞美。相比之下,城市人的语言却是干瘪的、干枯和单调的。沈从文感到,人与自然合一,才是这片山水奇异与秀美起来的真正原因,他笔下的生命呈现,似乎仅仅是为了活着,世世代代,生生死死,洋溢着生命的激情。“他们那么忠实庄严地生活,担负了自己那份命运,为自己,为儿女,继续在这世界上活下去。不问所过的是如何贫贱艰难的日子,却从不逃避为了求生而应有的一切努力。在他们生活爱憎得失里,也依然摊派了哭,笑,吃,喝。对于寒暑的来临,他们便更比其他世界上人感到四时交替的严肃4(《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沈从文笔下的这些生命积极活着的本身,体现的是一种生命的强力意志。生命有时虽然显得如此卑微纤弱,甚至愚蠢粗野,但他们生命的意义就在于这短暂的生命时空中丰盈的哀乐本身,一种近乎神性的对于生本身的执着与信仰。沈从文在他的散文中,从不避讳对男女性爱的描写,而在所有的性爱故事中,水手与妓女的形象十分鲜明。水手是强盛生命力的代表,“水手多强壮勇敢,眉目精悍,善歌唱、泅水、打架、骂野话,下水时如一尾鱼,上船接近女人时像一只小公猪。白天弃船,晚上玩牌,同样做得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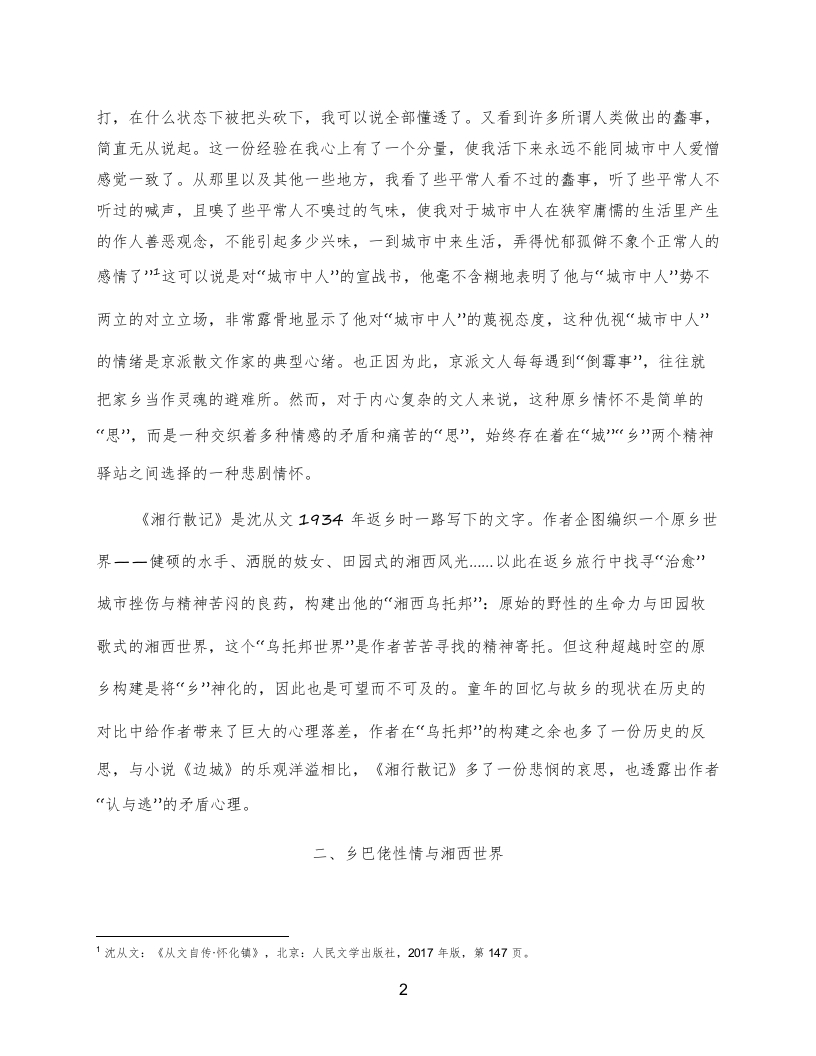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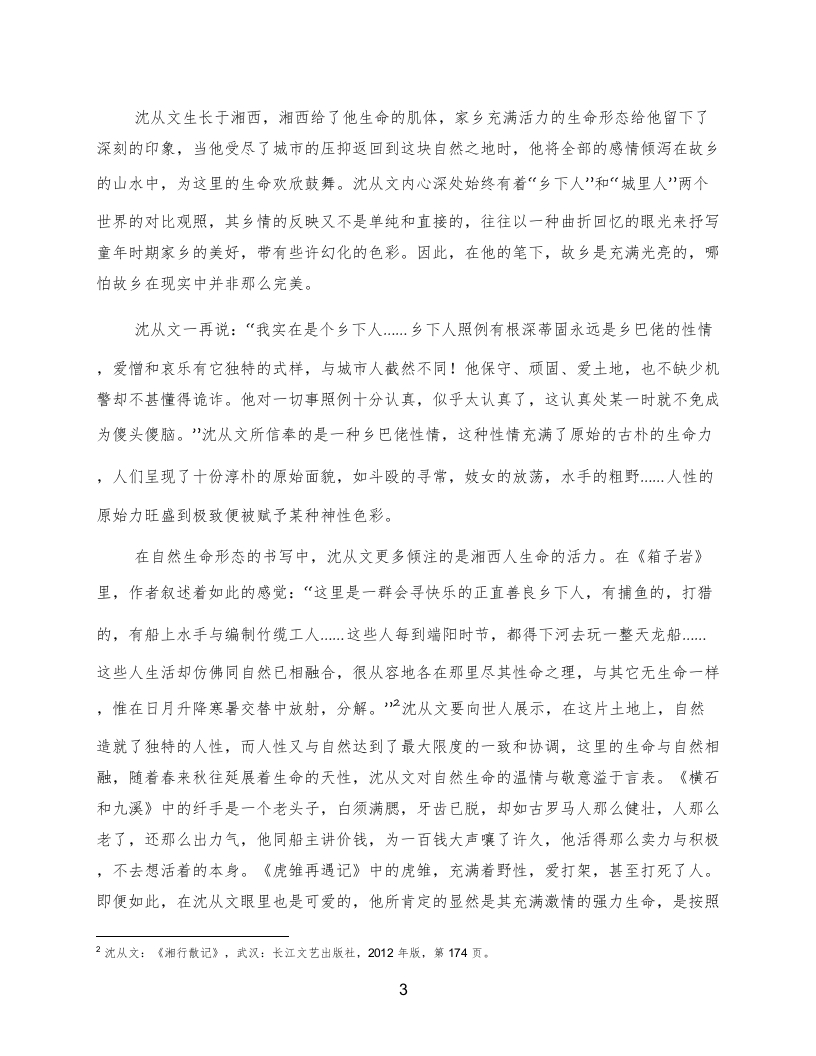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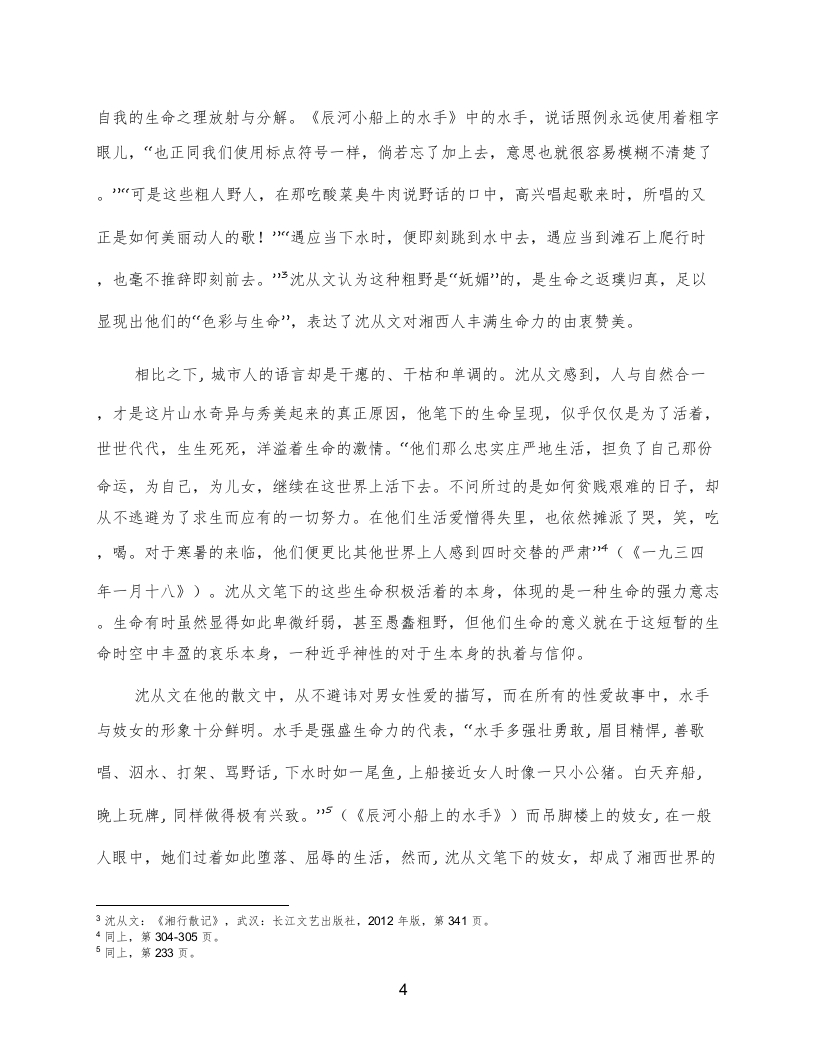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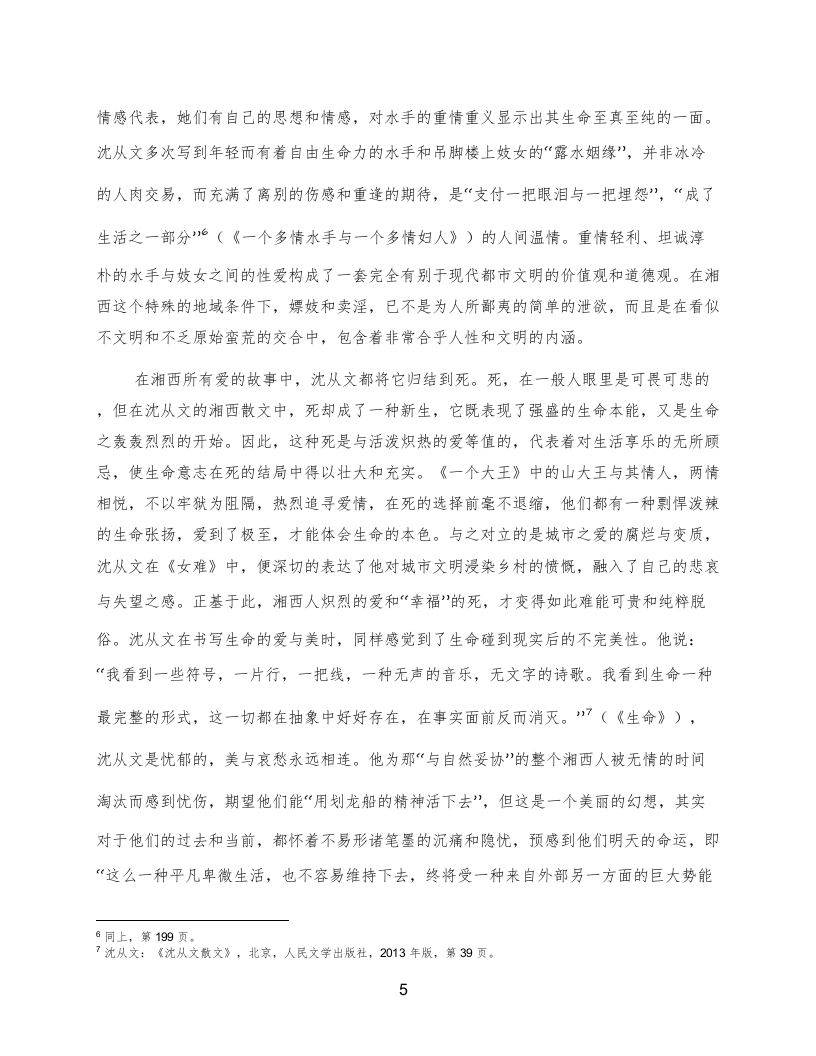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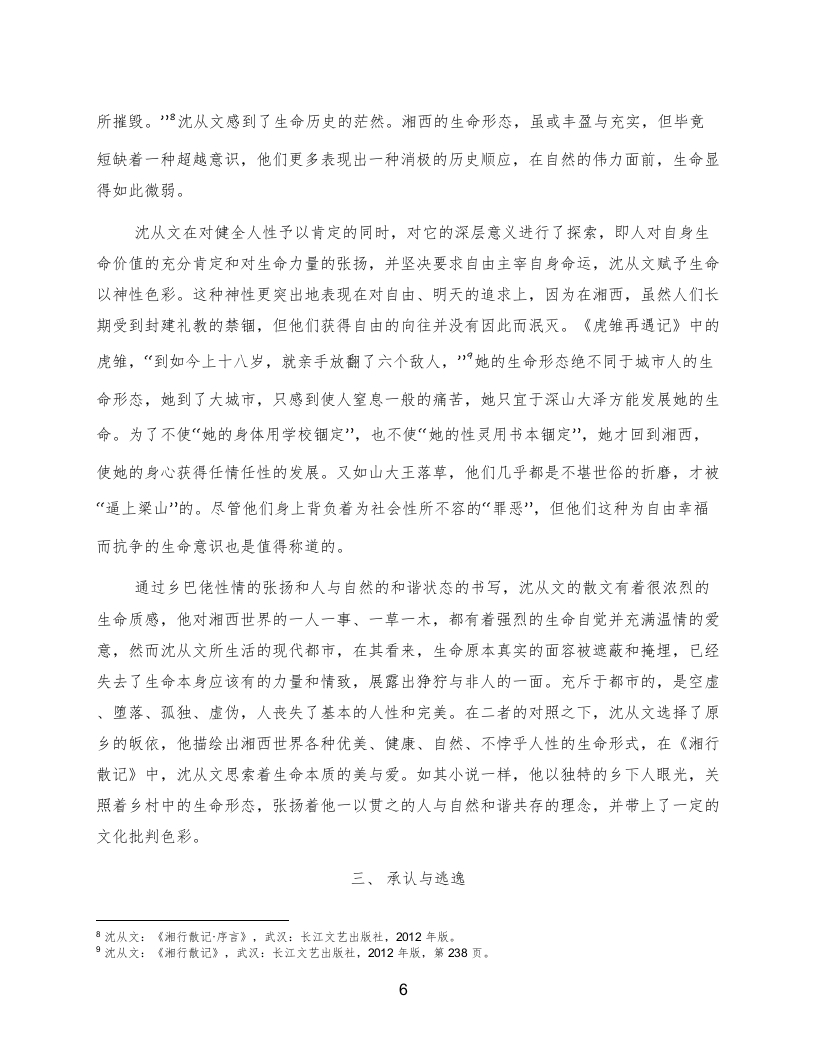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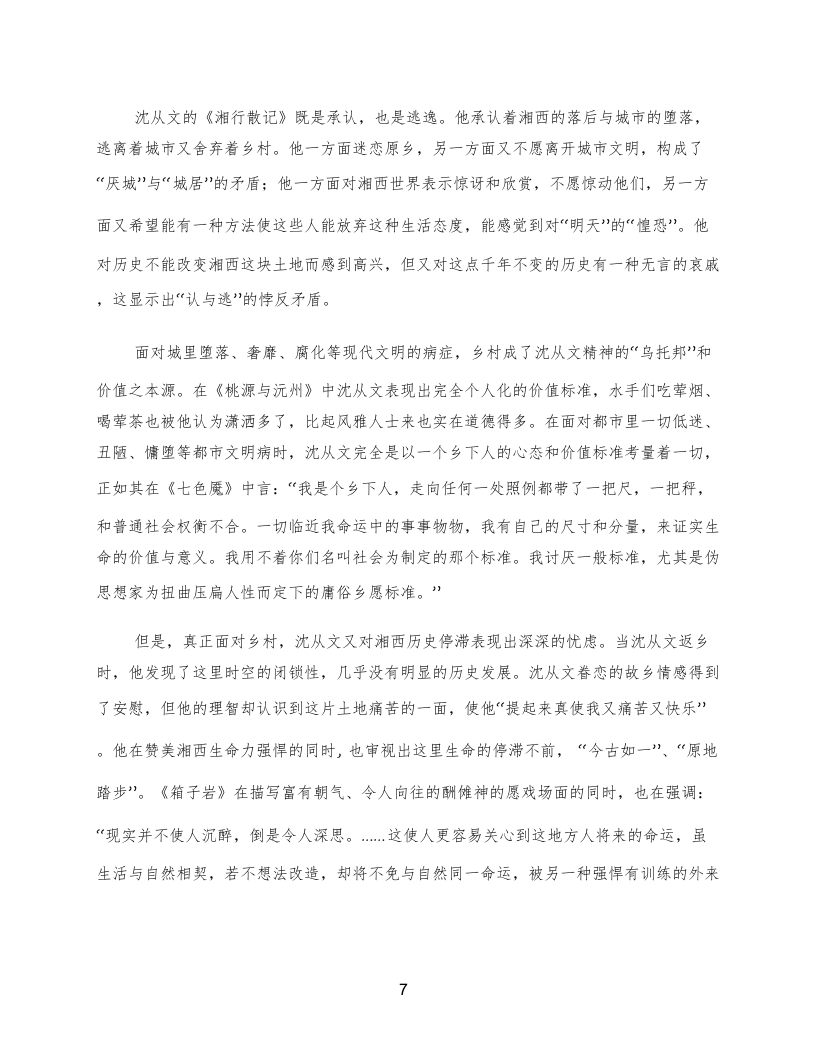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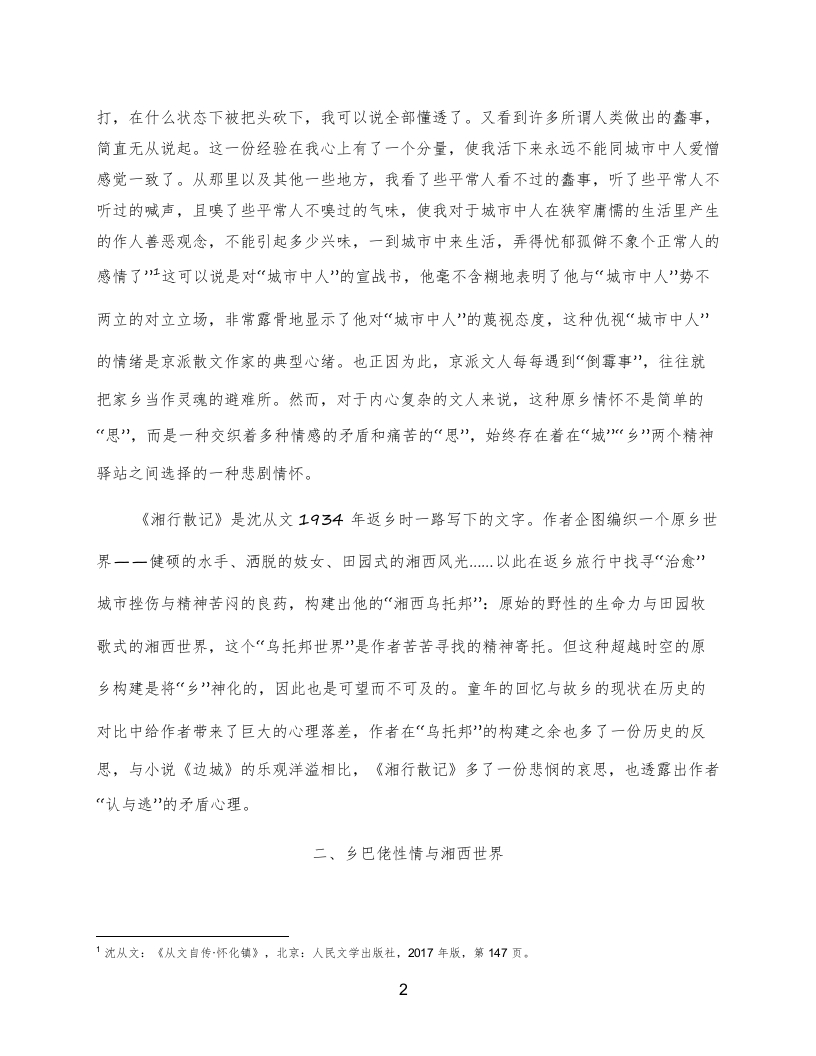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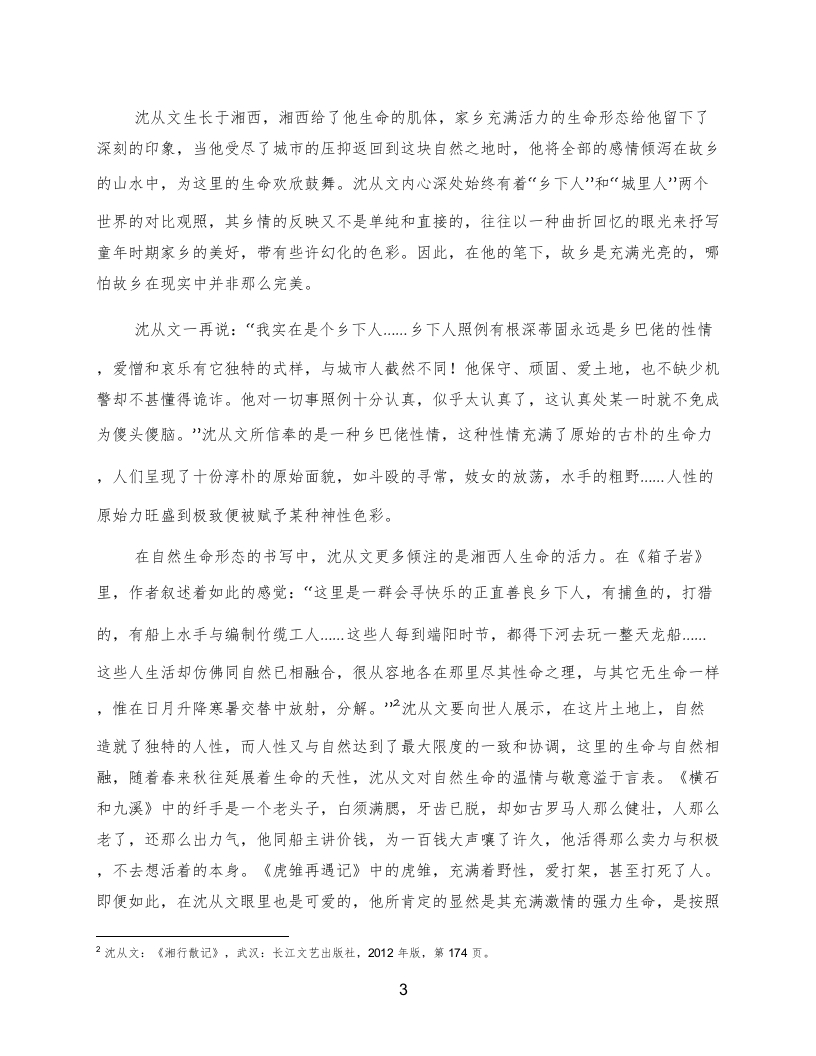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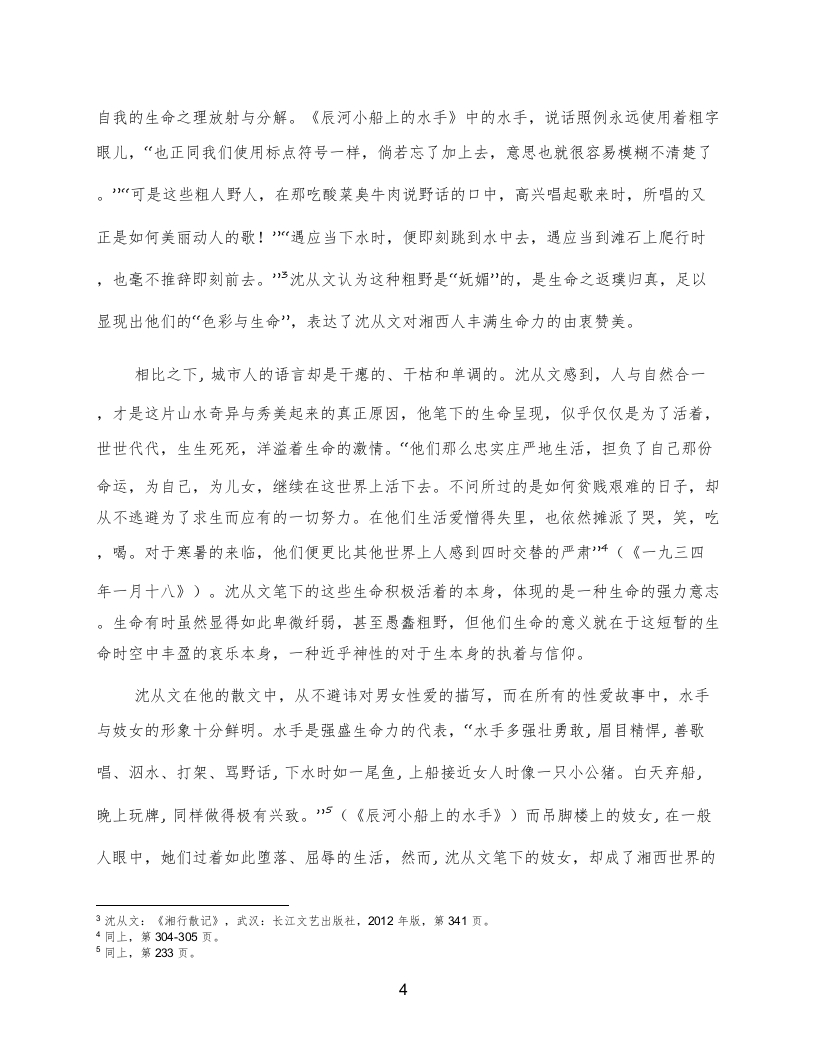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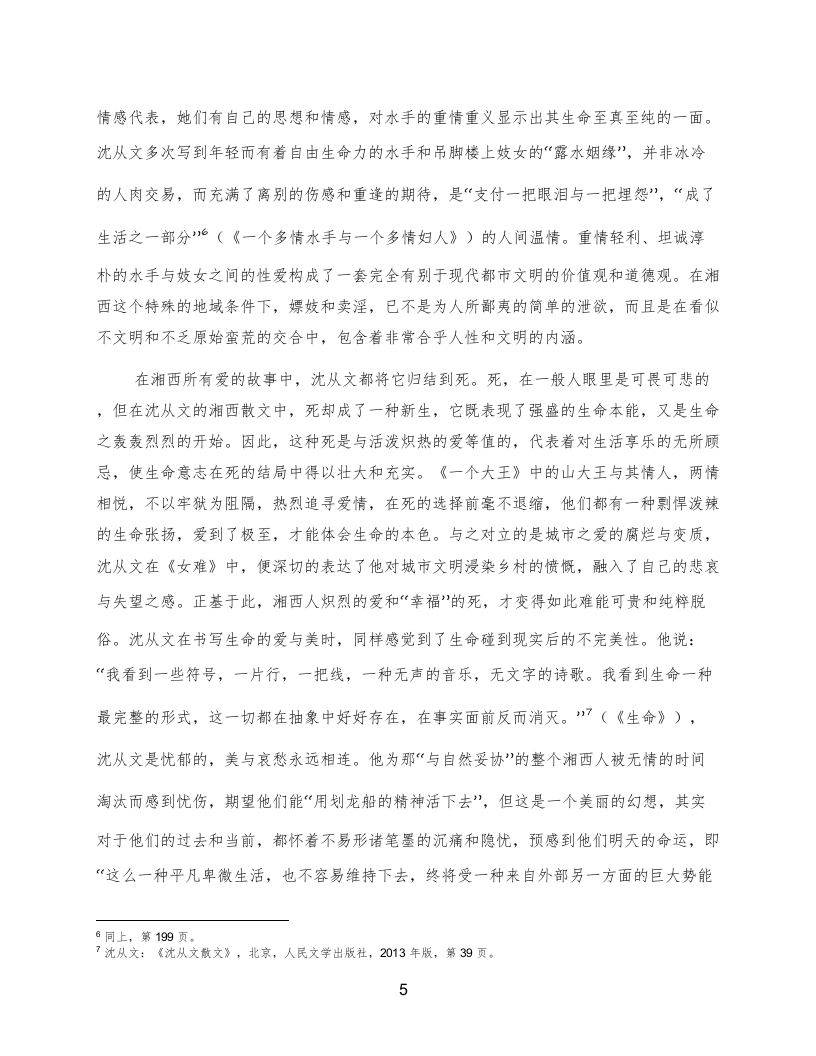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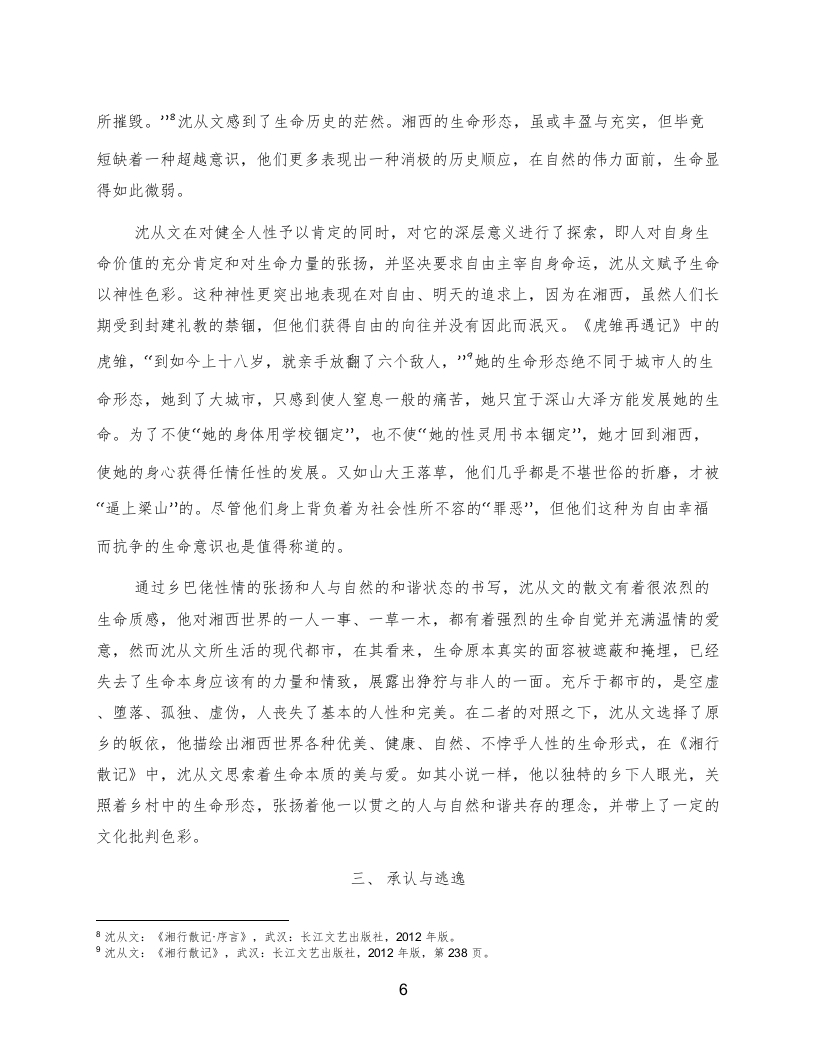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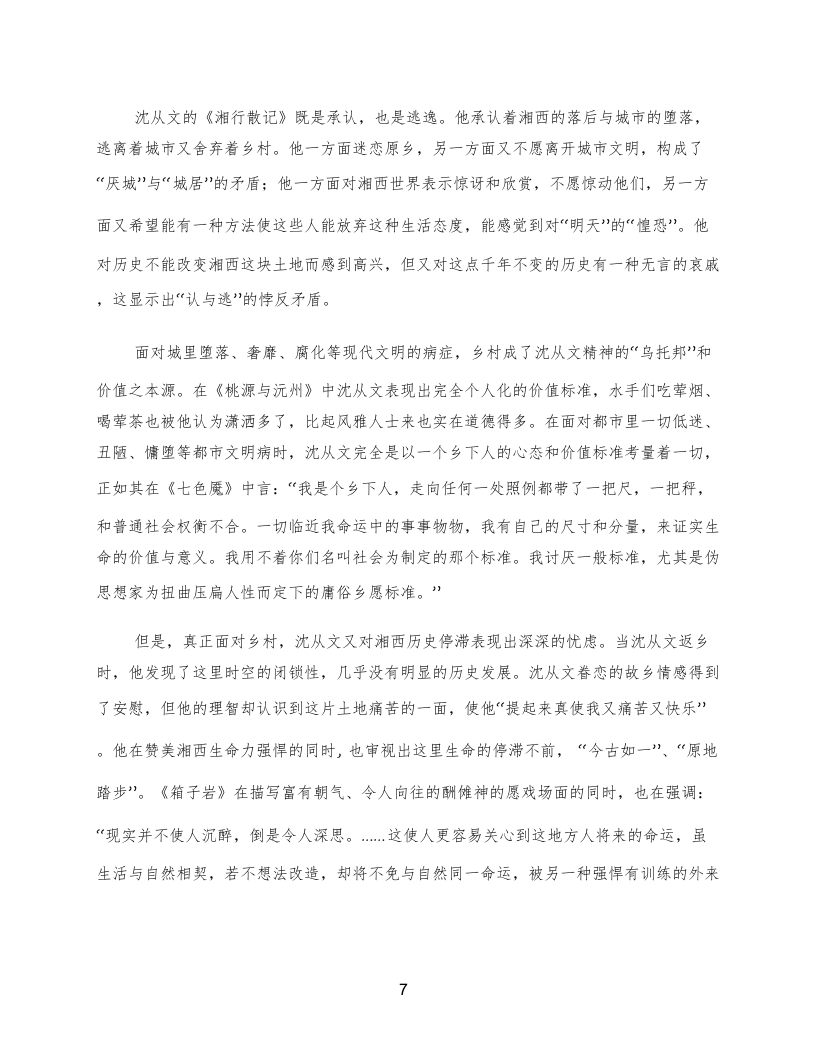
暂无评论内容